梁泉清:大花(小小说)
大花是一只狗,是小时候家养的一只狗,是一只母狗。
我是家里的老幺,上头有两个哥哥,两位姐姐。也许我太不争气,整天痴迷于捉虫捕鸟,偷瓜儿摸枣儿,完全成了哥哥、姐姐眼中的“坏蛋儿”。
那是个阶级立场十分鲜明的时代,他们读书的读书,种田的种田,割草的割草,每天从事着“高大上”的活动,自然就与我划清了界限。他们懒得辅导我学习,懒得过问我的生活,懒得听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经历”。

哥姐的疏远,让我一下子“瞄”上了大花。吃饭了,我与大花在老枣树底下,面对面地蹲着,我吃一口,就喂大花一口。我吃饱了,大花依旧瞪大眼睛,盯着我手中的饭碗。没办法,趁母亲不注意,盛上一碗,找一个僻静处全给了大花。
有时候,大花喝饭的“吧唧”声会招来父亲怀疑的目光,聪明的我常常从狗嘴里夺过饭碗,猛喝一口,朝狗腚上踹上一脚,骂骂咧咧——“讨——厌!滚!”
为这,经常能听到母亲的抱怨:“三儿,你就不能少喝一碗?你爹干那么重的活,今个又没吃饱,只喝了半碗饭!”我就纳闷,自己与狗边玩边吃,都喝三碗了,这么长的时间,爹怎么才……
上学了,就把书包带子缠在狗脖子上,往狗头上拍上两掌,大花就一溜烟儿似的跑在前面。我便邀上几个小伙伴,追着大花疯跑,常常是自问自答,一边跑,一边喊:“天上是啥?星——星!地上是啥?月——饼!河里是是啥?小——鱼儿!噗啦噗啦一小盆儿,噗啦噗啦一小盆儿!”那个饥荒年月,美食也成了孩子游戏的主旋律。
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下了学,带上大花打猪草。我们孩子是一群,狗儿们也是一群。大花是位伟大的母亲,小伙伴家的狗崽子大多是她的后代。大花自然是绝对的“领导”。
大花鼻子灵,在庄稼地里这儿嗅嗅,那儿瞅瞅,突然狂吠几声,往往会从灌木丛中窜出一只野兔。狗撵兔,这可是一台“好戏”。霎时,十几只狗如离弦的箭,围追堵截,从四面八方扑上那兔子,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兔子!”正在寻野菜的我们,把手中的篮子一丢,拿起小铲子跟在狗群后面追,而且边跑边扯开嗓门吆喝:“大花,朝北!黑子,从前面截住!虎子,加快速度!快,快呀!”
大花老谋深算,追着,追着,就拐了一个弯儿,躲在一棵灌木旁停下来。我就朝大花骂。还没等开口,那兔子被几只狗崽子“逼”得无路可逃。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居然杀了个“回马枪”,掉头儿往回跑。那些狗崽子们速度太快,收不住“蹄子”,等回过了神儿来,大花嘴里早已叼着兔子,在一个高高的土埂子上站定,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我知道,她在吹嘘自己的能耐,炫耀自己的功劳。
逮住一只野兔,不亚于过新年。我们把大花抬起来,庆祝“胜利”!轮流在狗脸上亲了又亲。自然,晚上就能吃到兔肉炖白菜,所有参与的小伙伴可都有份儿。

吃肉,是我们孩子的幸福时刻,也是狗儿们的节日。那一天,爹下田很晚,等把兔子扒了皮,放进锅里炖上,月亮早已爬上了树梢。院子里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孩子,还有那大大小小的狗。笑声、哭声、汪汪声,更多的是嘴巴的“吧唧”声,简直成了家庭集市。每位孩子手里拽着一只空碗,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爱犬,滔滔不绝地重复着白天的故事。
自然,我们这些孩子终于做了一回“馋猫”,大花和她的儿孙们啃上了骨头。
夜里,我破例让大花钻进自己的被窝,搂抱着狗头,睡得特别香,特别甜。
“兔子事件”过后,我赦免大花的“大逆不道”,恩准她可以和我睡一个被窝,一起进餐。这对于一只狗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荣耀。
吃饭时,大花倒是很谦卑,常常蹲卧在距我半步远的地方,张着嘴巴,竖起耳朵,伸长舌头,瞪大绿莹莹的眼睛,静静地望着我。待我吃饱喝足之后,用筷头儿对着那碗指了指。
人言狗语,心有灵犀。她极小心地晃了晃那高昂的狗头,慢慢低下去,紧贴着地面轻轻的朝前蠕动一下身子,粉嘟嘟的舌头一伸一缩,“吧嗒吧嗒”就那么两下,再看那碗,一个米粒儿不剩,比娘洗的都干净。于是,我就假装嗔怒,大声呵斥,一只手打狗嘴,另一只手悄悄从裤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窝窝头儿,对着那狗嘴顺势那么一搁。大花来个“鲤鱼打挺”,如同骡马下晌,两三个滚儿打过去,一个窝头儿瞬间就进了狗肚。
那段儿时间,家里的气氛怪怪的。不知怎么,哥哥、姐姐都不搭理我,还常常拿目光“剜”我,特别是二哥,看到大花,像见了仇人似的,动不动就用脚踢,拿棍子打。搞得大花神经兮兮,听到二哥的声音,就夹着尾巴,浑身哆嗦。爹似乎比平日沉默了许多,吃饭时,守着面前的饭碗就是不动筷子,“啪嗒啪嗒”一袋一袋的抽着旱烟。
直到有一天,爹从田里回来,还没有放下肩上的锄头,整个身子像刚刚擀出的面条,被风一吹,就歪倒在老枣树底下。大花第一个发出了信号,像个婴儿时的“嗷嗷”叫着,一个劲的用头轻轻地拱着爹。
我跑过去大声喊着:“爹——爹——你怎么了,呜呜呜,你怎么了?”二哥抬起腿朝狗头上踢了一脚,转脸又掴了我两个耳光:“怎么了!你心里不清楚?把爹的那份口粮都给狗了,这会子在这儿假惺惺!滚——”大花哀嚎着原地转了一个圈儿,跑出了家门。我则腆着肚子杀猪般的叫唤。

二哥蹲下身,掐住爹的人中,娘跪在地上,把爹的头轻轻放在她的腿上,大姐端来一碗凉开水,用小勺子一下、一下给爹灌下。爹睁开眼,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泥土,嘴里不停地责备娘:“哭啥?今个儿天太热,中暑了!别吓着孩子!”走到我跟前弯下腰,用手背为我擦了一把泪水:“三儿,爹给你逮了只青头蝈蝈,用野麻皮栓在了草帽沿上,刚才还‘吱吱吱’的叫呢!”二姐没听娘发号施令,就为爹炖了一碗鸡蛋脑儿,双手捧给爹。
二哥铁青着脸,找了一根麻绳,顺手操起一把铁锨。我一看,撒开脚丫子就往外跑,歇斯底里地喊:“大花,大花!快,快,快——跑!”二哥冲出家门,手中的铁锨如同离弦的箭,大花一跃而起,腾起的一条后腿还是被铁锨削到了。她一声也没叫,落地那一刹那,猛回头,两道近乎绝望的,溢满泪水的,哀楚目光刺疼了我。
“大花,快,快——跑!”尘土扬起,落下。一眨眼工夫,不见了大花。那把明晃晃的铁锨静静的躺在巷子口,锨刃处附着指甲大的血迹,那上面粘有一小撮狗毛。二哥顺着血迹最终没能追上大花。
我倒是躺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爹扬起老拳,在二哥脸前晃了晃吼道:“不就是你弟弟一天喂它两个窝头吗?大花也不该死罪!马上就到端午节了,放倒麦子,就不饿肚子了!快,扶你弟弟起来!
二哥浑身湿漉漉的,嘴里喘着粗气,望着骨瘦如柴,面部黝黑的父亲,抽泣着像根木桩,倔强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日子像小河里的水,哗哗的往前淌。过了端午就是芒种。没了大花,我像没魂似的,睡觉梦见大花;挎起书包,想起大花;端起饭碗,念叨着大花。见了二哥,就白瞪起眼睛,咬牙切齿,那不争气的泪水就从眼角处往外冒。
每次打猪草,在河提、沟沿、高粱地里仔细搜寻着,一见长有碗大的黑毛、白毛的花狗,就追上去,喊着“大花”,瞄上老半天,害的那狗对着我直汪汪。
高粱红了的时候,邻村姚村放露天电影,我和几个小伙伴怕父母不让去,下了学,来了个“先斩后奏”,挎着书包直接去了姚村。
电影《南征北战》看不到一半,老天不作美:一时间电闪雷鸣,乌云滚滚,稀稀拉拉的落着大雨点子。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出了村哪里能摸到回家的路?几个孩子瞎摸乱撞一起,七折八拐,钻进一片小树林里,头“呱唧呱唧”的不停地碰着树桩,就是出不了那片林子。最后,力气耗尽了,额头冒血了,连惊带吓,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身子抖得如风中的树叶,呜呜呜的小声哭泣。
突然,一个黑影窜过来,我吓得“哎——呦”一声,整个身子倒了下去,感觉身子下面有一个软软的、热热的、毛绒绒的东西,还不时发出熟悉的“呜呜”声,借着闪电的亮光,我惊奇的喊出来:“大——花!我的大花!”所有的小伙伴都止住了哭声。
“大花,你到哪儿去了?”方圆搂着狗头亲了又亲。
“有了大花,我们就有救了!”孬货一个劲地念叨。
“书上说,老马识途,咱们的大花一定认得回家的路!”发根拽住狗耳朵振振有词道。

我们用牙齿咬断书包带子,打个结,连在一起,变成一根长绳子。一端套在大花的脖子上,大花在前面带路,五个小伙伴拽着绳子,勾肩搭背,慢慢跟着大花移动。
走不到半个时辰,就发现有许多手电筒在前面晃,老远就听到爹的声音,大哥、二哥的声音,发根爹的声音……几个孩子像注射量海洛因,喊叫着,答应着,奔跑着,扑上亲人。
等回过神来,回头寻找大花的时候,茫茫暗夜,哪里有大花的影子?
……
大花又一次消失了,直到现在,大花再也没有回到梁坊老家。大花也许不知道,“电影事件”之后,就有吃不完的白馍。如今,爹、大哥、发根爹、孬货爹相继离开了人世。
大花,你去了哪儿?是旷野、树林?还是地狱,天堂?四十多年来,你常常就在我梦里……


作者简介:梁泉清,山东省东明县第四实验小学语文教师。与书结缘,神安、心安、教安。曾作自嘲诗——“写作教书吃饭,粉笔讲台黑板,师生朋友习惯。永不自满,挑战自我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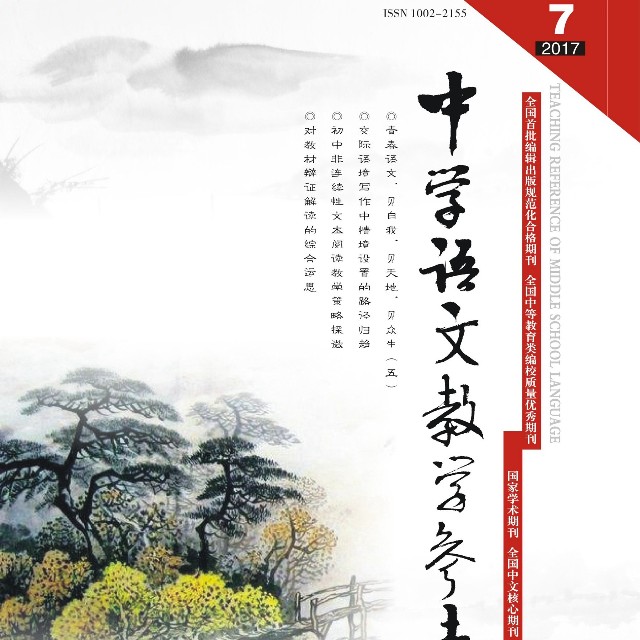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