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吃货苏东坡 风流帅的生活令人向往
如果说,一个男人,一辈子都在“耍”着帅,而且帅出一个音乐名词——高八度,让女人暗里着迷,让男人拜倒辕门,非东坡莫属!
他曾写道:“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说真的,他实在太谦虚了,其风流帅何止三十年前,何止这长安弹丸之地,即使千年后,他依然风流帅,后世也有很多中外佳丽要穿越千年嫁东坡。李白曾对他的偶像暧昧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姑且我对偶像苏哥也如此暧昧一下,用三句歌词来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一、“踏平坎坷成大道!”
苏哥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州其实是其颠沛流离,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命运这一巴掌把他扇进了一条坎坷崎岖的羊肠小道,可在跌跌撞撞中一不小心踏出了康庄大道。命运的黑手给了他一副枷锁,他却能让人生舞起来,而且是跳着探戈、恰恰和芭蕾,一种从容潇洒而又活力四射的美,艳羡得令人流口水。
一个超级吃货出现了,岭南的荔枝要吃,会须一吃三百颗;黄州的猪肉立马也有个艺术范的美誉——“东坡肉”,什么“慢著火,少著水,火侯足时它自美”,什么“早辰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惠州的羊也倒了八辈子的血霉,连骨头都被我苏哥给烤串了,撒点孜然,一个“羊蝎子”竟然嚼出了阳澄湖大闸蟹了味道。
海南岛上海里的小动物生蚝吓得退潮后都不敢在海滩上晒太阳。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恐怖的是我们的苏哥,要吃就要吃出心跳感,心脏不好的,接下来这几句可以跳过。竟然烧蝙蝠、啃老鼠,有诗作证——“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所有种种不仅是免费版,搜山捡海入舌尖,百味不用一钱买,而且是不限量的绿色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个吃货,吃的越多越奇越漫长,恰恰能证明两点:
一是他的“人生囧态无穷歇”。苏哥的人生恰如一“轼”字,那时年轻的苏哥潇洒地驾着摩托车开足马力,却不想一路颠簸一路囧。要么没油熄火了,要么车刹坏了,要么撞到电线杆了。种种“屋漏偏逢连夜雨”狗屎运似乎永远在青睐着他,让他越贬越远,差点贬出中国掉进太平洋!
二是他的“生命境界更逍遥”。他在黄州开垦出一片精神自留地——“东坡”,于此修篱种菊,苦修密炼进而顿悟,林语堂在《吾国吾民》曾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他从那一刻也拈花微笑了,因为曾经的苏轼死了,脱胎换骨出新生命——苏东坡。
什么也困不了他,因为他的灵魂会flying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又因为灵魂的飞升,苏哥发现原来距离是可以产生美的,在飞升的过程中,一路的坎坷辛酸、跌宕起伏看起来也美了。他还发现飞在不一样的高度和角度,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渺小的尘埃可以超越。

苏哥的确变了,从一个诗人变成了一个美学家。命运这块寒冰一遇到他的心,便化了,被艺术性地审美化、趣味化了。这种穷吃、囧吃竟然吃出了五星级饭店的高大上:有品味、有文化、有境界。命运这把冷刃,一握在他手中便瞬间被镀成了金灿灿的,闪着温暖的光。这一种经营生活的超强能力和超好心态让生命活出了真谛:自由、自在、自趣。
我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上帝、与他人无关。他成了真正的“苏子瞻”,瞻者,望也。看得淡、远、透、美。这才是一种真正的风流帅,一个万里挑一的自由灵魂、有趣灵魂踏平坎坷,踏破桎梏,持着彩练当空舞,舞出“赤橙黄绿青蓝紫”般的人生色彩、精彩和风采!
二、“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是的,苏哥活出的风流帅是一种青藏高原般的高度,这个高度是由坎坷的经历、超凡的才华、圆融的智慧、崇高的人格四块基石构建而成。
在这里,简单聊聊苏哥的后两块大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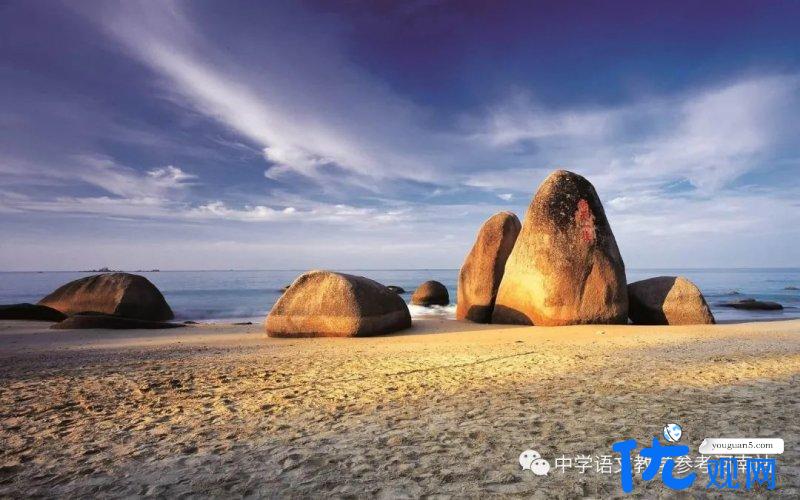
真正的智慧也许不是指向外在的,去发现自然、宇宙等的奥秘然后去征服它,而是指向内在的,去发现自我的秘密。就像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的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也像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东西早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是人自己。中国的禅家也有类似说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汝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心向灵山塔下修。” 佛法也好,佛也好,告诉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追求不要舍近求远,其实就是身边,在自己身上。
苏哥的IQ高,高就高在他最终选择从认识自己,超越自己那突破,因为只有超越人自己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那么所有的一切皆可“一览众山小”,小到尘埃里。
原来一个人的大自在、大快乐,不一定是在高处,在人生的顶峰;还可以在低处,在人生的低谷。从悬崖坠落低谷,不应像一个玻璃瓶那样粉身碎骨,而应像一个弹力球那样,坠撞谷底的那一刹那,反弹出人生的另一个高度。
原来人自身可在心中修炼成“金钟罩”和“铁布衫”,不惧外界一蓑烟雨。原来心安就好,处处是可以栖息的家乡。“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那么心如何反弹、栖息、心安?也许,一念转通罢了。
苏哥的头脑里曾经有两个人在掐架,一曰主,一曰客。在《赤壁赋》里最终聊得很欢,两个吃货干翻一船美酒佳肴,然后醉眼朦胧,相视一笑,就这样夜不归宿,一觉睡到大天亮。
原来世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遭际都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不能是一根筋想不开。正像苏哥的一首哲理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思维之山的框架与束缚,就别有洞天。
赤壁的夜晚,那澄澈的江水,那皎洁的明月(其实是他自己)给了他自己一念通的答案。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无论长短、逝存,物我一样,不必羡慕。同样人生的顺逆、起伏、荣辱、穷达、福祸不必艳羡与深悲。他想通了这一点,发现快乐不必舍近求远,真正的快乐是发现当下的美,享受当下的自在,因为大自然也有无尽藏也可共适。
人生真正的痛苦解脱非他救,乃自救。念转,心转,境转。则可“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苏东坡对自我的评价)。”
而崇高的人格在于,苏哥永远是一枚暖男,带着一颗慈心看世界,看众生。
无论新旧党政PK得如何火热,他永远有着超越党争的清醒。私利放两边,道义摆中间。这一为民之大义,就是所谓当权者的一肚子不合时宜,但苏哥从未后悔过。
他一路贬过的地方处处莲花香,留下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在徐州当起了前线防洪抢险总指挥,搭一茅棚于江堤,惊涛拍岸之时,独立居守安民心,最终保住了徐州城。离别时,曾动情写下:“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流放密州,蝗灾、旱灾、洪灾等灾情似乎为了一睹我们苏帅哥的风采,竞相慕名而来。
苏帅哥撸起袖子带领百姓加油干,热烈欢送了它们。
流放杭州,当起了园艺设计师,疏浚西湖,修建了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让城内外的游客可以气定神闲地近距离欣赏美女——西子。
流放黄州,大兴慈善,当上了孤儿院院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孤儿院。
流放惠州,改善民生,设计了广州最早的自来水供水系统。
到了海南,当了校长兼班主任、语文老师,办学堂,普文化,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来到儋州跟苏轼学习。并培养出高材生,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
这是他的风流帅,永远以一颗赤子之心,悲悯情怀去造福一方,唯独忘了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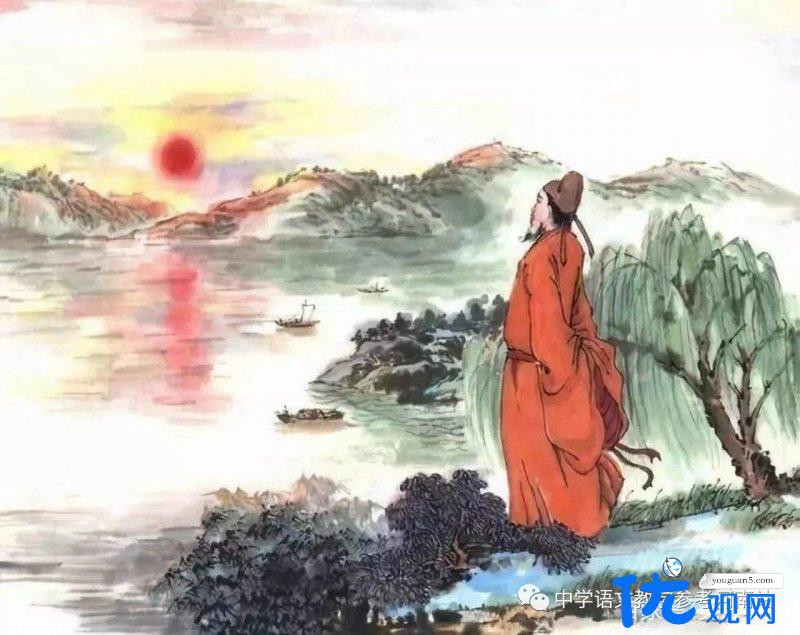
所以,苏哥简直不人!是什么呢,用在他眼中是一坨屎的好基友佛印的话来说,“我看你像尊佛!”他就是一尊行走于世俗的活佛。他在黄州这棵菩提树下觉醒顿悟了,用智性自救自度来完成对苦难和困境的解脱和超脱。用慈性去救他,度他——悲悯四方众生,善待各地百姓。苏哥一路颠沛流离地走着走着,人生成了“经”,自己成了佛。
“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让后世的无数的fans带着虔诚靠近他,感受他,找寻活着的真谛。
三、“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我们的苏帅哥曾对三国的周瑜周帅哥羡慕得口水流下三千尺。什么“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什么“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但有一样,我们的苏帅哥一点也不输于周帅哥,他有三位红粉佳人,完胜他一个小乔。一位百年不遇的奇才,若少了三位奇女子的陪伴,那将是人生的一种遗憾甚至是灾难。
三个女子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她们似乎都是上帝精心安排来到他身边的天使,一个接着一个进行接力赛陪着他走过人生一程又一程的跌宕起伏,百转千回。这是苏轼不幸人生中的一抹暖色,慰借着他孤独的心,只是太匆匆,林花谢了春红。

一个男子被三个女子着迷一生,这是怎样的一个富有魅力的男神啊!
一个男子一颗心里同时容纳下三个女子,这是怎样的一种深情啊!
在他生前,她们用一颗真挚的心来陪伴,呵护,可以说她们对他,有一个最平凡而又深情的字——“懂”,这是世上最温情的语言。王弗懂他的口无遮拦,不善交际和识人,常于屏风后指点一二。王闰之懂他的忧伤和痛苦,用温柔撑起了温馨的家,度过了家庭最低谷的时期,可以说她是真正的贤内助。而王朝云虽和他相差26岁,但她懂他的一肚子“不合时宜”,更懂他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她会为他的词而哭泣,而感动。
而在她们死后,他用一颗炽热的心来思念、守望。可以说他对她们,也有一个最珍贵而又深情的字——“愧”。他似乎是个讨债鬼,克妻命,命运不仅捉弄了他,连他所爱之人也“爱屋及屋”了,红颜薄命逐流水。
曾经的“唤鱼联姻”成就他与王弗的一段姻缘。于她死后,搁笔了三年,没有写下一个字、只是蜀山中多了一个痴情人攀登、浇灌的默默身影。那亲手种植的三万棵松树已亭亭如盖,在明月伴着清风的夜,摇曳的一声声松涛是爱的呼唤,令人断肠。
王闰之死后,他也实现了生前的旦旦诺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因为她陪伴了他人生最重要的25年,特别是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唯有死同穴的陪伴,才能还清欠下的债。
王朝云死后,他曾题一对楹联于惠州西湖的亭上,无限地感慨知音就像枝上的柳绵吹又少,“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那个“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小女孩,真的像一片云永远的飘走了。于她走后,那一曲她生前最喜唱的《蝶恋花》词,“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便成了耳旁的绝响。
这三个女子,一朵是花蕊,一朵是花瓣,一朵是花蒂,美美与共,熠熠其彩。她们都是一朵花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苏轼就是那个赏花人、惜花人、葬花人。他与她们彼此遇见,用心交织的美好爱情便穿越了千年。这样的风流,永不被雨打风吹去。
斯人已矣,但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东坡居士!生命的硬度、韧性在散发着光,生活的自在、自趣在温着热,让这一路上的坎坎坷坷,变成了寄情生命的山山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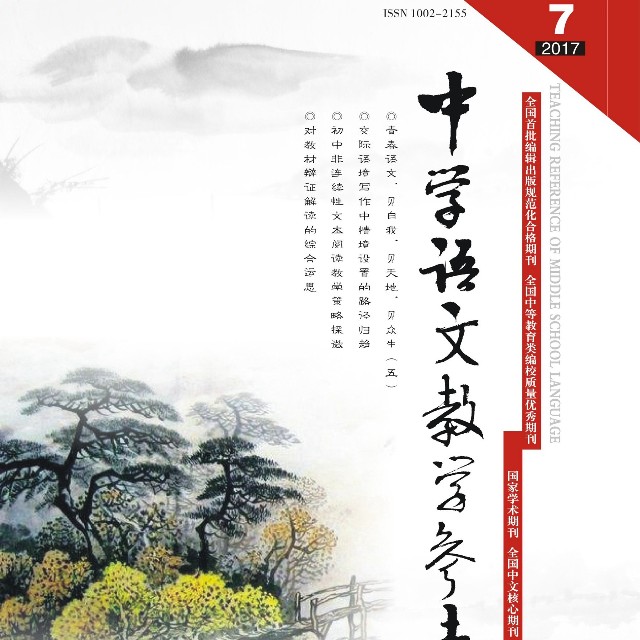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