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良:最轻也最重(感恩母亲)
那年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母亲得了病,在家里僵持着死活不肯上医院。我赶紧回到家,见母亲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脸色发黄泛白没有多少血色。
母亲见我回来了,眼里有道亮色。我摸摸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妈,咱们去医院吧!”我责备说。母亲张张口:“输点液就好,去医院多花钱。”我伸出手抱起母亲:“别犟了,妈!还是去医院看看,我也放心。”
一抱,好轻啊!8岁的儿子我都快抱不起来了,60多岁的母亲轻轻一抱,像捆柴,不费力就抱起来了。

在县城人民医院诊断,脑梗、冠心病、心肌缺血、肺炎,什么症状都有。医生连番用药,却成效不大。
我心里难受,便询问母亲想吃点什么。母亲回答说:“医生一直让喝点粥,嘴里什么滋味都没有,就想吃点酱豆腐。”
待我买来,却撞见了查房的医生。于是,这几块小小的酱豆腐,在母亲渴望的眼神中被我丢进了垃圾桶。
母亲的病情依然不见起色。
一周过去了,母亲开始催我上班,说:“假请这么长时间,领导肯定不高兴。又赶上高三,会影响学生学习的。”
我哭笑不得:“你怎么不怕影响你的病呢?”母亲对我笑笑:“我感觉快好了,放心吧!”
夜色笼罩着整个医院,也弥漫到每个病房。我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她的身体怎么那么轻?
过去,母亲围着个褐色大脚盆洗衣服,三四十斤的脏水一下就抬起来了。在上高中的我的眼中母亲显得很“巍峨”,可那时的我怎么就不懂得去搭把手呢?
我嘱咐母亲一定要听医生的,便带着小心回到学校。不想刚过两天父亲又打来电话,说母亲吃什么吐什么,连水都喝不进了。
赶到医院再看母亲时,她脸色发黑而且双目无神。母亲见了我想装做笑笑,可也只是嘴巴动了动。我为母亲翻了个身,她轻的厉害,像张纸。我的眼眶一下子溢满了水。

主治大夫将病历表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用笔帽挠挠头皮说:“什么药都用了,我也没办法。”
没法子,转院吧。
第二天凌晨,我们搭上高铁前往郑州。下了高铁,我又背上了母亲。还是轻,轻的像羽毛一样根本感觉不到。只有耳侧时不时传来细微的呼吸声仿佛有种魔力,增加了母亲的重量,增添了我心头的希望。
地铁正值高峰,来去匆匆的都是上班的人。我要替母亲找个座位,她微微张了张嘴,声音很虚弱:“大家都累,算了吧。”
工作在外,母亲把所有在外打拼的人都当做自己的儿子,怕大家累着。工作在外,我却不知道常常联系她。
不知道母亲腰椎、颈椎怎么样了?不知道母亲何时犯上了脑梗,得了冠心病?不知道母亲何时感染上的急性肺炎?
我满心皆是愧疚。母亲却连声要我把她放下来,说自己太重怕压到我了。我的母亲啊,都到这个时候还想着自己的儿子。
我骗她:“已经放下来了。”母亲两只脚乱划,试图触碰地面。我赶紧说:“妈,别走太快,我扶不住了。”母亲的脚才慢慢停下来,但一只腿微弓着蓄力,另一只腿照旧朝前划着。
慢慢地朝前划着。无力,但执着。
我的母亲啊,我的眼前雾气重重。水雾遮住眼镜,遮住了前行的道路。
我知道母亲心中儿女最大,我也知道母亲一开始不愿去医院是怕拖累我。可等到我也想像母亲一样“巍峨”地背起她的时候,母亲却“轻”的不想增添我的负担。
到达医院的时候,母亲的身体有点发重,不似先前那么轻。这时,母亲好像又有了力气,要下来走走。
我有点高兴,便让母亲一个人坐在候诊区。取了预约单,我抬头看着电子屏幕里跳动的候诊通知,想起路过病房楼时走廊里排满的病人床位,心里愈发没底。回头看看母亲,她冲我安慰般的笑了笑。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来了位脚步生风的女医生。她年纪跟我母亲差不多,我心中一阵喜悦,忙将病历和CT递给她。

对着荧光屏,苗医生细细看了一遍。然后她告诉我:“肺部阴影面积大,黑斑多,估计是肺病。病人住院复查才能确诊。”
我问:“我是外地的,不知还有病房吗?”苗医生说:“有,我来安排。”闻听此言,除了感激,我觉得母亲的微笑似乎就是转好的预兆。
母亲住院后,就急急地催着我去吃东西。因为儿子开心而带给自己的快乐,这快乐驱使她强撑着也喝了半碗稀粥。
又是一个医院的夜晚,夜色沉沉却给人希望。我将一个编织袋铺在地上,每隔半小时就按照医生的嘱咐给母亲量一次体温。
借着轻柔的灯光,我凝视着母亲不再发黑的脸庞,细听着母亲起伏有致的呼吸声,感觉心里从未有过的平和与幸福。
想想母亲白天的笑容,太熟悉了。

从小到大,我就是在这样鼓励的笑容之下,一个人走夜路上下学,一个人摔得鼻青脸肿也不哭,一个人学习工作遭遇多大困难总能找到宽慰处。
小时候有次高烧不退,母亲喂过我药后就紧紧地搂住我微笑地哼着儿歌。整整一个下午,母亲的手没有撒开过。
我的身体忽冷忽热,冷时母亲的体温温暖了我,热时汗水浸透了母亲的衣服。我的身体时不时一阵抽搐,但只要依靠着母亲,我的心里就特别安宁,烧也就慢慢退了下去。
母亲是世界上最重的人,像座山,可以依靠。
我大了,母亲老了。
这些年老得尤其快:先是头发丝变老,一根一根的,一片一片的,怎么染也黑不了;接着是气力变小,原来走路风风火火地就像苗医生,如今站久了头就偏到一边急促地打摆子;母亲确实老了,她经常想不起要跟我说些什么……
母亲也是世界上最轻的人,我要像座山,让她可以依靠。

第二天下午苗医生看过各种检查结果,确诊为大叶肺炎。在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药水瓶的点点滴滴的注入中,母亲苍白的脸渐渐有些血色。
我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来到病房走廊的尽头,压抑了许久的泪水也终于流了出来。
母爱最轻,又最重。它轻到平时让我们觉察不到,但到了关键时候,它又会猛地压到我们心灵最脆弱的地方。
母爱最轻,又最重。因为它最轻,所以它最重。

作者简介:
余良,息县第一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淮水怀情,濮山孕朴;龙门探幽,谯楼雅望。息州古国,栖身于此;一高学苑,立命之所。观无涯学海,日升日落;记风俗物事,息壤息歌。有人生点滴,品书论时;存乡土故园,依稀山河。拙笔一枝,书生一个;薄酒一杯,赤心一颗。以文会友,原创之作;知交之心,相识相得。著有个人教育随笔集《耕耘,永无止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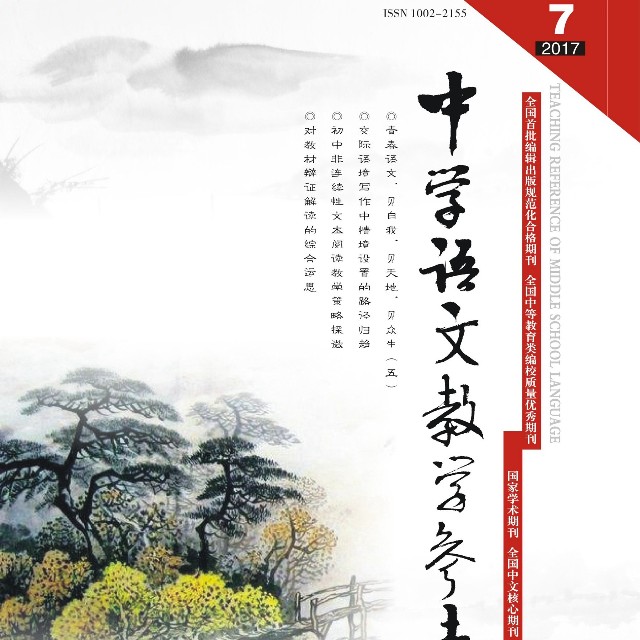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