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小说家里藏着几个小说家 几层故事
《刺杀小说家》并不是这个春节档的爆款。
它的题材和类型,放在当下市场,似乎有些事倍功半。
不过,创作者花了五年时间来精心打磨一个“重工业”项目,这才称得上是电影创作上的正道、正宗。
所以,他们完成了一部更电影的电影。
空文一纸,包罗万象
友情提示:本文是基于电影《刺杀小说家》的过度阐发,内含剧透,适合观影后或二刷前阅读,或可获得某种“互文”的趣味。
头回尝试写小说那年,想起小时候一个场景:
七八岁那年夏天,一日独自在家,躲院里的煤棚玩战争游戏,用木头、砖头、铁钉和毛线、泡沫等废料搭起战场,几只塑料兵人分了阵营,情节与台词全靠一张嘴嘟囔,当然也包揽了音效和内心独白,噼里啪啦,咚咚锵锵,啊我死了。
主角不只死了,还被钉上十字桩,遭了剐分了尸,哪怕他弹尽粮绝之际领悟了盖世神功,施展乾坤大挪移,也最终难逃厄运——只因彼时的我心情沮丧,眼见天色已晚,父母仍不回家,天偏又下起滂沱大雨。
那几年家中境况不佳,父母为谋生陷于困顿,我虽懵懂无知,亦有所感,禁不住伤春悲秋强作愁。至今记得,在惶恐焦躁的极点,我冲出煤棚,跪在雨里仰天嚎啕,扮演幻想故事中的绝望场景,口中咒骂,也在祈求。
是幻想的英雄上了我的身。我的恐惧敷衍幻化出他的悲剧,他的命运成就了我的中二。

△大概就是这样的,在细雨中呼喊。
这段记忆再次回闪,是看完《刺杀小说家》后出神的片刻。当然,这么多年过去,恐怕除了那雨中绝望的几个瞬间,其他细节都是意识的重构和表演了,所谓“内心戏”是也。
此类经验,人人皆有。但也正因过于平常普遍,一般不被细究,即便想起,谈笑间也就散去了。不曾想,一部奇幻电影(至少一半是奇幻)触及了这份宝贵的经验。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刺杀小说家》在一众春节档电影中,以异类姿态向观众发出了邀约——直接参与一次造梦的过程。而且,在讲述一个“编故事”杀人或救人的故事同时,电影本身似乎就是一个修辞表达,暗含着某种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哲学。

《刺杀小说家》无疑是春节档里最注重文本的一部(图为路阳与杨幂在片场对剧本)
对于观看者,这是一层更近的“贴近”。毕竟观看一部电影,不如进入一部电影。
呈现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其关键问题在于让观看者相信这个世界中“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只有如此,才不会出戏,也就是常言说的“相信这个设定”。
巧妙,且意味深长的是,《刺杀小说家》的设定就是基于上述问题,比一般电影多出一层“套娃”,观众知道自己正在看电影故事,而电影故事里还裹着一层故事,类似《盗梦空间》的结构,但比《盗梦空间》多出了一个情节驱动机制,同时让观众看到梦和造梦者,现实与虚构形成“互文”关系,现实的“两江市”与小说的“云中城”互为变量,相互影响。

现实的“两江市”与小说的“云中城”互为变量,相互影响。
随着两个世界层层展开,观众很快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空隙向自己开放,不经意——也可能是不得不——凭借自身经验去补足隐藏的可能性和意义。
由此,观众的“脑洞”,与电影文本也形成了互文关系,共同实现更为丰富的意义,或提出更多元的问题。这是《刺杀小说家》过于概念和符号而略显空泛的原因,但也是它内涵饱满可以细品之处。
人生如踏上冒险旅途,现实可以催生幻想,幻想可以改变现实。
这个陈词滥调的设定看似“一纸空文”,却也可谓包罗万象,举一千从,就像那些由远古人类构想却深植于每个现代人潜意识里的神话原型。
因此,无论是小说家与小说世界,还是观众与电影之间,相信“意淫的力量”,是进入电影《刺杀小说家》的钥匙。
手握这把钥匙,我打开的脑洞之门是:“小说家”,究竟是谁?
第一重可能的故事是这样的。
路空文,曾经是个活跃的年轻人,性格并不“古怪”,也不啃老,家境大概也不错,毕竟父亲是神灯公司合伙人,成功的商人。大概率父亲也是个不错的父亲,所以他当年风光的照片一直摆在路空文书架上。
或许也正因此,父亲的意外死亡——大概率是“意外”——才给路空文留下巨大创伤,变成了不求上进的无业青年,最终躲进小说的幻想世界。
电影提示说,父亲死于好兄弟好伙伴李沐的谋杀,这极有可能是一起牵涉巨大利益的商业谋杀。而且,我们不难看到,神灯公司一边向用户许诺美好未来,一边通过社交软件窃取隐私,李沐虚伪笑容的背后是大资本家的贪婪和无耻,高科技掌控时间空间,不过是渴望权力和不死的“造神”行为。
路父可能就是因反对这种不正义而死,理念不合遭排挤,挡人财路被谋害,这种情结既很“小说”,也很现实——说不定就是遭投毒而死呢。

躁动一时的“游族网络CEO被投毒”案,证明了大公司宫斗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还奇情
补足小说家的这段“个人小传”,观众只需多想一步,因为路空文直播的小说虽是玄幻武侠题材,但立意并不算隐晦:一个凡人少年空文多年来茫然逃亡,但不得不承担起哈姆雷特式的沉重命运,接近杀父仇人赤发鬼,弑神,报仇。
银幕上也一次又一次地,将小说家生活的“两江市”与《弑神》中的“云中城”迭化显现,正是两个次元破壁的标记。
云中城的赤发鬼一死,两江市的李沐就(可能)会死。这个设定第一次提出时,雷佳音饰演的关宁代观众提问:这是他妈的神经病?

△“小说改变现实”是整部电影最点题的一句话。
小说里少年空文向赤发鬼逼近一步,李沐果然就头疼晕倒。这又一次的破壁时刻,或许暗含了一个并未直接交代的信息:对父亲“意外”之死的蹊跷,路空文并非真的一无所知。
更可能的是,六年前幼弱的他承受不住刺激,产生了心理回避,压抑着那一点怀疑或真相,逃入幻想世界——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情节里泄密。
若是提出弗洛伊德来过渡,未免俗套,但这确实是理解文艺创作原理的一种简易道理,所谓“相由心生”。
这一点补足,或许正是李沐多年来念念不忘要追杀路空文的原因,这孩子就算不是谋杀目击者,也极有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线索。因此,借关宁制造一起“完美犯罪”来斩草除根的动机确实算是立得住。
双雪涛的小说原著里,刺杀者和小说家有这么几句对话。(小说家)我没工作,原因说来话长,脑子出了点问题。
(刺杀者)没关系,你呢,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从一个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好像月亮突然失去地球的感觉。
月亮突然失去地球的感觉?
是啊,就是这样感觉。
很不错的比喻。
以前很少打比方,说什么就是什么,开始打比方是出事之后的事情,因为许多事情突然说不清了。
写小说,就是打比方,有意无意的做比喻。
往彻底了说,若不是语言文字和脑内的隐喻,人是无法生存和认识世界的——无论你是不是小说家。
现实遭遇困住了人,潜伏的信念催生了幻想世界。小说家路空文如此,失去女儿的关宁——也就是刺杀者——也如此。
路空文不断让自己写下去,只有信任写作,相信那个世界,他的生活才有意义。曲折的情节走向是潜意识的反应,卡文写不动是自我怀疑,但信念仍在,这信念几乎要突破次元壁,现实里无力复仇,小说里早晚写死他。
关宁的困境也有普遍意义,他“一直在等希望,希望一直不来”,无望几乎将他逼疯。或许是现实里不敢面对“女儿可能已死”的真相,梦里才有了象征希望和恐惧的云中城。
一个在电脑上敲,一个在小本上记。信念和执念都有了生命力,突破次元壁,少年空文是路空文的自我,红武士是关宁的自我。

李沐是否会后悔,找了一个对亲情有执念的人,去刺杀另一个对亲情有执念的人?
小橘子,正如李沐所说,开始可能只是名字巧合,但渐渐变成了路空文和关宁幻想的融合。
这些是电影基本显现出的文本故事,但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关宁根本不存在,他和他的故事——寻女、刺杀以及杨幂饰演的屠灵,也是小说家想象出的分身。观众看到的整个电影故事才是路空文的小说,一个延宕纠结虚实相生的复仇故事。
第二重意淫,小说家路空文和他的《弑神》,是被现实困境逼疯的关宁幻想出来的,他才是“小说家”。
现实故事是关宁追杀人贩子失败,被警察误抓,唯一的女儿照片也可能失去。这是一个孤独中年男人所不能对抗的绝望。
破壁的起点,是黑色轿车里的屠灵打开车门,那个逃出警车扑进副驾的男人已经不是关宁,而是关宁创作出的主角,而他遇上的转机就是神灯公司、屠灵和路空文,每段情节都是他对不同自我和现实挫折的比喻。
残缺的梦和至死不放弃的执念,令人进入一场臆想,这种事其实常有发生。我有个朋友曾患有抑郁症,那段时间总觉得有人在窃听和跟踪,而他列举出的蛛丝马迹,竟很合逻辑,补足细节就是一场有头有尾的戏。
就像无法应对现实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并非真的疯狂,而是执念难以融洽于社会现实,不得不以“讲故事”的方式自洽,一番硬抗熬挺过来,最终发现“杀人”和“自杀”都非问题解决之道,唯有干掉心魔才有活路,也就是“弑神”。

弑神,是红武士、少年空文和小橘子联手完成的。
也或许,关宁早就是一半疯狂了,坚持的人有时候就是一副看似疯狂的模样。他在小本上记录的梦,是这些年来记下的小说片段,是他“弄丢女儿”的自责和悔恨,也是“重逢女儿”的梦幻与渴望。
小说《弑神》里的小橘子无父无母,于是他分身出少年空文保护女儿。少年空文和他一样茫然无措,小橘子正是他的引路人。最终,身为刺杀者的自我也进入《弑神》世界,杀死心魔赤发鬼,摘下头盔,与小橘子重逢。
比起一切都是关宁疯梦的故事,另一种可能是,只有刺杀小说家的情节和《弑神》是关宁的幻想,现实仍在,电影最后通过小橘子之歌找到女儿是真实的。
不过电影终究没有留给女孩一个清晰的正面镜头,结局温暖但仍是开放的。而老板是否因赤发鬼被杀就真的死掉了,也并未直接交代。
这样结尾里,可能隐藏着一个潜在作者:杨幂饰演的屠灵。她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她才是那个小说家。
在银幕外的现实,一名儿时被拐卖或被抛弃的女孩,很可能再难有机会与父母重逢相认。就像父亲执着于寻找女儿,女儿也可能活在对父母的复杂情感,加之幼年时曾流浪和孤独面对险恶世事的经验,她写了一部复杂的小说。
小说中有大老板李沐和他罪恶的神灯公司、小说家路空文和他的玄幻小说《弑神》,还有多年来不停寻找自己的父亲,而她自己则化身踟蹰在爱恨之间的中间人“屠灵”。
屠灵这个角色身份很有意味。
她处在刺客与小说家之间,同时也处在刺客和老板和刺客之间,几人的命运走向似乎就在她的念头变幻之间,这正像一名“作者”的身份,一介凡人能否弑神,屠灵站在哪边是关键。
屠灵这个怪名字也很有意思。
在我的过度解读里,“灵”即是人“意淫的力量”,讲述自身故事和认知自我的力量。因此屠灵的任务即是贯彻老板意志,确保关宁杀死小说家的“完美犯罪”实现,屠杀“灵”的力量。
或者,也可以将屠灵误读为“图灵”。计算机历史上著名的图灵测试,也就是Turing test,其目的就是测试人类造出的机器(傀儡)是否能拥有自我意识,进行独立思考。这样说来,甚至可以揣测,在这部小说里,屠灵其实是神灯公司基于流浪儿改造的一名人造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杨幂的表演不恰好冷冰冰如机械傀儡吗。

杨幂塑造了一个她之前从未演过的新鲜角色,就像《终结者2》里的T-800。
有一种吐槽,说神灯公司培养一些奇怪的打手,还有屠灵这种毫无来由的打女也不知从哪学的功夫,由此可见这电影实在太胡扯。
这么说没错,特异功能,投石神技,打不死,冷冰冰,这一切都在暗示:这不是真实,是虚构,是藏在屠灵背后的作者,把对父亲的想象写成了最终勇于解开面具的红武士,而那个陪伴小女孩的流浪儿,就是她童年流浪时的经验,在小说里变成了保护小橘子的少年空文。
屠灵就是小橘子,小橘子就是屠灵。
所以屠灵对关宁说,要是我爸爸也像你一样,我就不会遇到李沐了。
那么,“云中城”和“赤发鬼”又可作何理解?
对照神灯公司和帝王般的老板李沐是一种理解方式,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明喻。也可以有勇士斗恶龙之类的神话原型的理解方式。或者,你可以说是古代,是历史,是某个喊打喊杀的残酷社会的象征,这都说得通。
电影里有个未展开的留白,路空文告诉关宁,说自己写了一个角色,但没写好,那是个戴着面具看不清真相的人。
这人是谁?

郭京飞在片中既饰演黑甲,也饰演“老僧”,为后者上妆至少要花6个小时。
放在几条故事线里都可以解释。他可能是无力面对现实的关宁或路空文,也可能是最终摘下面具的红武士,或越战越勇的少年空文。按照我上面的意淫,这人也可能是小说家屠灵的自我指涉。
不过他是谁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特性:一个“看不清楚真相的人”。这么一想,这个人或许说的就是我,是你,是每个进入这部电影的观众?
阅读一篇小说,观看一部电影,就是自我经验投射的过程。这是接受美学的逻辑,通俗的解释也不复杂,故事给你的信息,和你原有的信息交融,构成了完整的意义。
有人在云中城两坊厮杀中感到了热血,有人在两眼杀气的小孩脸上感到了恐惧,有人在红武士的“人间大炮”猛击中发泄了压抑,还有人从赤发鬼和李沐身上意会出了对双重权威的愤怒。
当然也可以说,电影创作团队改编文本,做视觉特效,以及表演都在丰富和诠释原著小说。

△郭京飞以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饰演”妖怪“黑甲”。
这是个尝试去“看清楚真相”的过程,也正是电影创作和小说文本之间的相互生发,观众经验和电影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层隐秘,才让电影《刺杀小说家》略难进入,但也非常值得玩味。
其实谁是小说家,也不重要——只是我的一连串意淫罢了。我自认比较重要的,是激发我这些意淫的一段富有象征的场景。
少年空文用意念驱使了黑甲,将一件本要杀死自己的“魔物”变成了拯救自己,为自己而战的武器。我认为,这可以算是电影《刺杀小说家》的“题眼”所在,它生发出的意义,足以容纳以上我全部的扯淡。
基于这个“题眼”,我更愿意把《弑神》和整部电影理解为人的自我觉醒和对日常的反抗,而空文意念驱动黑甲,也象征着文本虚实相生的内核。
电影《刺杀小说家》英文片名是《A Writer's Odyssey》,暗示这个故事在呼应希腊史诗《奥德赛》,讲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漂泊归乡的冒险之旅。在罗马神话里,奥德修斯就是“尤利西斯”,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应该知道,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经典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就是与《奥德赛》的呼应,讲了一个苦闷中年男人在都柏林彷徨游荡的一天。
这自然让人理解为一种主题暗示,少年空文所经历也是一场奥德赛式的冒险旅途。他和神话里的奥德修斯有着同样一个对手: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

△希腊神话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是海皇波塞冬之子,而在奥德修斯的旅程中,被奥德修斯刺瞎了独眼(图为意大利画家佩莱格里诺所作的相关题材)
不同的是,在我的理解中,《弑神》里的独眼巨人分身成了两个,一个是独眼“黑甲”,一个是巨人“赤发鬼”。
如前所述,赤发鬼的巨灵神般的外形、残忍的吞噬和碾压之力,令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动一动指头就能摁死凡人——你几乎可以把他理解成任何恐惧。
不一样的是独眼“黑甲”,它本是奉命追杀空文而来,后又化为碎片寄生在空文肌肤之上,吸着他的血,也受着他的影响,直到某一刻,突然被这凡人的意念掌控了。
恕我再进一步扯淡的误读。
我固执地以为,“黑甲”就意味着庸碌琐碎的日常对凡人无可逃避的追杀,它无时不刻消耗人的生命力和热情,令你疲乏不堪。
这让我想起王小波在《三十而立》中经典的比喻:我......忽然觉得生活很无趣,它好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曝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得乌珠迸出。生活也如是:你一天天老下去,牛皮一天天紧起来。这张牛皮就是生活的规律:上班下班,吃饭排粪,连做爱也是其中的一环,一切按照时间表进行......
王小波的湿牛皮尚有时间表,如今的日常生活里,连时间都已被淹没,只剩得一团虚无。
我记得少年时看《死亡诗社》,曾为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老师Keating而振奋,他让学生站在讲桌上,换个角度看世界,并告诉他们,梭罗说“大部分人过着平静而绝望的生活”,因此不要逆来顺受,要破茧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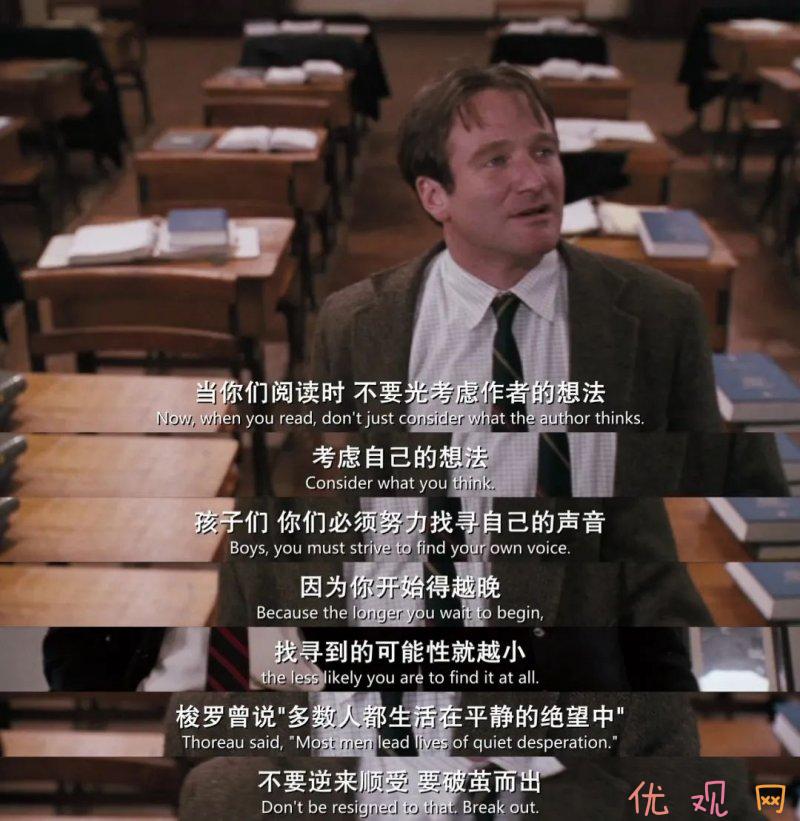
△电影《死亡诗社》中的经典场景,Keating不也说了吗,不要只考虑作者的想法。
这句话1854年梭罗在反思现代生活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中所写,原文后面还有一段话,著名作家徐驰这样翻译——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两者中都没有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
一百多年后,这段反思仍然适用,它说的就是那张湿牛皮,也是“黑甲”,或者是流行词所说的内卷社会中“电池人”的生存状况。
我那位得抑郁症的朋友,曾和聊起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的一个观点,说人所有的焦虑其实源自根深蒂固的死亡焦虑。从幼年到青年,再到中年老年,是不得不直面死亡的过程,因此唯有不断地自我阐释所作所为的“意义”,才能对抗这份焦虑。
写小说、画画、拍电影、任何一门艺术或有自我认同的事业,都是这样。每个人的意义感必须通过自我叙事完成,才能避免成为异化的工具。
赤发鬼临死前痛苦的呐喊——“我不想死,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神也逃脱不了凡人的焦虑,谁让它是人造的呢。
如果这么看,人人都是少年空文,或人工智能“屠灵”,时时刻刻要面对加缪式的存在困境,选择顺从或反抗,选择被碌碌庸常消磨,或是创造存在的意义。
人人也确实都是小说家,都有死线(Dead Line),在死线到来之前,都要不断写自己的故事。这当然并不是说人人都要去真的写作,成为小说家。这只是打一个比方,需要你自己解读一番。
竟然扯了这么多,显得很中二。
我想起很多年前,有个朋友曾说我满脑子奇怪的想法,疯疯癫癫像个中二。那时我不理解中二一词的意思,以为他骂我是中年二逼。
现在明白了,他其实是在夸我勇于反抗。


 影形人
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