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张尕怂:我的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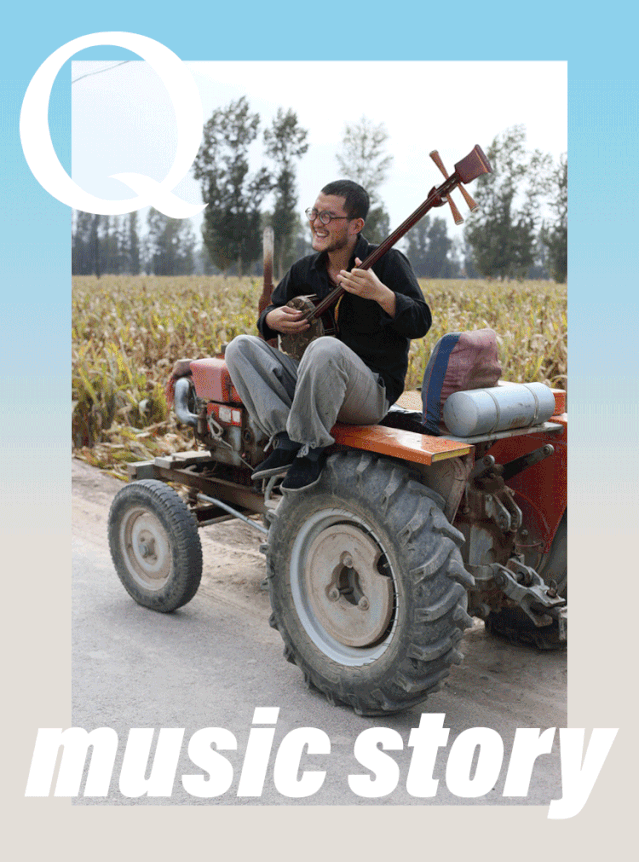
张尕怂生于甘肃白银,现居云南大理。虽然长年进行民歌的采集和创作,但他身上一点没有民歌考古的历史负担,用他的话说:“我就是玩嘛。”但这个“玩”从他大学退学起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张尕怂的记忆里,小时候家里住得特别偏僻,也没有电视和录音机,接触的音乐只是在别人结婚的时候放的一些外面的流行乐,或者过年从打工归来的人口中能听到一些。后来去县城读书,他接触了摇滚乐后开始学习吉他,并在上大学时组了一支没什么固定风格的乐队。那中间的三四年,张尕怂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家乡特有的声音。
而直接的转变要从张尕怂退学说起,他什么都没想,学也不上就直接走了,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地走。张尕怂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在行走的过程中采集民间音乐这个事对他来说算是正式开始了。此前他也在网络上进行过一些“采风”,但从可以检索到的民间音乐中收获的见闻与行走中的近距离感知是截然不同的。

在采风过程中,张尕怂并不只在意自己是否录下了什么珍贵的音乐,而是先和那些老人们唠家常,听他们讲过去的事情,张尕怂则和他们唠自己在城市里看到和听到的故事。聊聊天、吹吹牛、弹弹琴,这种自然而然的交往甚至让他觉得比音乐本身更为动人。
每逢张尕怂回老家,到哪儿都随手拿个录音笔,走到哪儿随时都可以录音。只要打听得到的他都会去,走得多了就知道哪里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了,民歌的地图已经长在张尕怂的心里。“村子里几个老汉在巷口下棋,几个娃娃玩‘吃鸡’游戏,我喜欢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有帮助。我从小就健忘,所以喜欢记录事情。”即使如此数十年坚持走下来,张尕怂依然觉得对于民间音乐自己才挖掘了个皮毛。
相较于直接从文本出发的音乐人,张尕怂觉得自己的经历和沉淀是比创作更为重要的东西。他的方法是不停地走路、不停地采风,写歌的过程相对也会比较自然地生出来。他的作品一部分是将学来的民间音乐原样地唱出来,一部分会利用已有的曲调加入自己改编的歌词,还有一些从作词到作曲都是张尕怂原创的......简单来说,将自己的感受放进那些触动人心的旋律里是他一直秉持的创作理念。

而现在的张尕怂已经不单纯局限于采集音乐了,照片、影像、对话,看到啥好玩的他都要采集下来,甚至美食也可以。有些时候,在听到一些纯粹的自然声音时,张尕怂会认为这已经是一段完整的音乐,无须人的视角去介入。有一次,他在宁夏一座刚建成的寺庙里听到了铃铛的声音,当时庙里挂着很多铃铛,张尕怂便录下了铃铛和风的声音。在老家的时候,他不会放过哪怕一个背景聊天声,那些音景对他来说声声入耳。
这种自然而然的创作状态似乎和张尕怂从小受西北民俗文化耳濡目染有关。在当地的庙会仪式“社火”中,就有“锣鼓不响,庄稼不长”这样的说法。“闹一下,为了来年的收成。在仪式中人本身就很放松,每个人的眼神、心神都在发光,这和民间艺人唱民歌的状态有关,是一种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感觉。
这种状态中本来就有‘气’,‘气’就好像是人干活时候的劲,人高兴的时候也很有劲。”张尕怂如是说。在张尕怂的音乐里,有非常多极其细微的描写,比如专辑《泥土味》中的那首《姐姐》,寥寥几句歌词写尽人生中的肝肠寸断,这种特殊的敏感除了生活的经历外,可能也与某种天性有关。他回忆有一次帮三叔筛麦子,呛人的味道起初让他十分难受,但后来忽然意识到原来麦子被机器破碎时散发的那个味道才是真正的泥土味。

因为弹吉他的关系,总有人把张尕怂定义为民谣歌手。但他认为自己和民间艺人没什么两样。民间音乐有两个部分:一是酸曲,唱的是情情爱爱;二是用来记录历史的。
张尕怂的音乐就充满他对社会现实的记录,他甚至认为民间音乐的意义就在于书写真的历史,而这也是每一代民间音乐人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在张尕怂身上的体现并不是沉重的,反而更像随口说出来但又切中命门的表达。
今年过年,大多数人禁足在家,张尕怂也不例外。到了正月初八,家里存的年货不够吃了,饭桌上的菜也从原来的十几道变成了寥寥三四个菜。张尕怂的妹妹随口说了句“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我应该多灌二斤酒”,张尕怂就顺着这个句式结合自己的想法即兴玩出了那首火爆的疫情金曲《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

张尕怂在音乐中的即兴状态与随意表达也和他所受民间音乐的影响有关,流传于西北的民歌形式“花儿”就是其中一种。每年到了“花儿会”这天,青年人就会背上干粮到附近的山中去“漫花儿”,“漫花儿”不拘泥于形式,可以单打独唱,或一问一答互相对唱,非常自由“散漫”,所以叫作“漫花儿”。
而张尕怂的音乐也带些散漫意味,有时候像一个和你相熟很久的人总在你耳边唠叨他的所见所闻一样,有时出现的无词哼唱又会拉出一张悠长梦境的大网,对于张尕怂来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
5月1日,张尕怂释出其抗疫三部曲的终篇《甘肃有个大夫叫霞霞》,这首歌将笔触转向自己的姑姑霞霞在疫情爆发的当下毅然选择去一线奋战的事迹,表达了对医务工作者的关爱和对至亲的担忧和祝福。
接下来,张尕怂将要带来和布鲁斯音乐融合的全新力作,这也是他签约十三月旗下厂牌新乐府后的第一张专辑。和以往出自他手的纯民间音乐专辑相比,这是一次更国际化、制作更精良的尝试。他强调布鲁斯音乐其实也是一种民歌形式,在歌词内容上同样充满各种“土根”的描写。

张尕怂显得很轻松,他说在大理的时候,他也会把西北的民歌和大理的民歌糅合在一起唱奏,不知怎么的就是特别好听。另外他将再次与说唱融合,但这里的“说唱”听上去指的并不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现代说唱音乐。用他的话说其实中国早就有说唱了,在陕西和一些老师傅聊天时,他发现他们本身说话就很有节奏,而方言又具备旋律性,这已经是在说唱了,说和唱已经在一起了。
张尕怂大概花了十年时间才把生活过成了这样:三个月在外采风,三个月在外巡演,剩下的半年就待在大理,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为什么这样的状态需要十年时间来调整?张尕怂的回答依然很干脆:“在我这里没有刻意的取舍,我的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Qthemusic
Qthe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