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承认运气的存在吗?

图源 Christina Animashaun
利维坦按:没办法,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就是,这世界必然有人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勺长大的,如果把这作为所谓先天条件的话,那么,他(她)的未来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仍旧是未知的。同样,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底层人士来说,也是如此。
诚如文中所言,“一个人从人生这张彩票中得到的好处越多,否认这是张彩票的动机就越强烈”,这也导致我们在对待他人和自我的评判时产生了很大偏差。有人之所以对运气归因论有反感,部分原因在于这似乎是对他(她)自我奋斗的一种诋毁——其实仔细想想,如果你将偶然(运气)和必然看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或许就清晰很多了。

图源 Forbes
2018年7月,卡戴珊家族年仅22岁的继承人凯莉·詹纳(Kylie Jenner)登上了《福布斯》(Forbes)杂志的封面,那一期杂志的主题是白手起家的女性富翁前60位,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如果詹纳没有出生在健康、富裕、有名的白人家庭,她是不可能获得此等成就的。她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化妆品公司——据《福布斯》报道,该公司目前的估值为9亿美元——这不仅依靠努力,还有赖于强大的运气为基础。
大约在同一时期,时尚媒体《Refinery29》发布了《用每小时25美元在纽约过一周》(”A Week in New York City on $25/Hour”),这是一篇网络日记,作者是一位由父母支付房租和账单的女士。事实证明,如果你没有任何必要支出,每小时25美元能过得挺阔绰的!
这些事件刻画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享受着无数不劳而获的优势却故意不承认,哪怕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幻着形象——但在数十年的不平等程度加剧后,它又彰显起了自己的存在。
自然,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完全有动机忽视运气。他们视特朗普总统为“守护神”,他曾声称,“我父亲在1975年给了我一笔非常小的贷款,我把它建成了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这句话的前后两个分句都不正确。但在这件事和其他很多件事情上,特朗普的行为成为了一种掩护,它意味着人们依然可以坚持讲述这个神话。
最近的这些争议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成功与运气:好运与精英神话》(Success and Luck: Good Fortune and the Myth of Meritocracy)。该书认为,运气在每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本应是一个相当平庸、无法引起争议的观点,但许多评论家的反应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震怒。在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上,斯图尔特·瓦尼(Stuart Varney)气急败坏地对弗兰克说:“你知道当我读到那篇文章时,那有多侮辱人吗? ”
许多人在别人提及自身的运气时会感到愤怒,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这不难理解。在个人奋斗时将好运考虑其中会伤害我们的自我概念。它会削弱我们的控制感。它会引发各种各样令人不适的问题——关于对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的义务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是一场不可回避的战斗。停战是不可能的。就个人而言,与好运达成妥协是世俗层面的宗教觉醒,是建立任何自洽的普遍主义道德观的第一步。在社会层面,承认运气的作用,为人道的经济、住房和监狱政策奠定了道德基础。
建立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要反思自己的运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在面对他人不可避免的抗拒时要表达的感激和应尽的义务。
所以,这里给诸位送上几点提示。
我们最终获得的成就和地位有多少要归功于我们自身?
对于我们一生中最终获得的地位和成就,在道义上,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我们自身?反过来说,有多少要归咎于我们自己?我指的不仅仅是凯莉·詹纳或特朗普——而是我们所有人。任何人。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反映出你的道德观。大致来说,你越是认为我们的人生归功/归咎于自己,你就越倾向于接受默认的(通常是残酷、不公平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人们基本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你越是觉得我们的人生并不归功/归咎于自己,你就越是相信我们的人生轨迹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外力(和纯粹的偶然)塑造的,你对于失败就越有同情心,你就越希望从幸运的人那里得到回报。当人们认识到运气的存在时,削弱它的严酷影响就成为了基本的道德工程。
要理解运气的作用,首先要解决由来已久的“先天与后天”之争,这一话题一直吸引着公众,与其说是因为科学,不如说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更深层次的存在主义问题。

图源 NPR
“先天”已经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大致指代着我们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部分,我们的躯体、基因——已然射出、有着既定路线的命运之箭。“后天”则意味着我们改变的能力,我们被环境、他人和我们自己塑造的能力,在既定的命运之路上挪移乃至逃离的能力。它是我们对自己命运掌控范围的缩写。
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误入歧途的观点。
你身上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
当然,你的基因、你的发色、你的基本体型和外表、你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大自然赋予你的东西是如影随形、无法摆脱的——而大自然在降下天赋时,并非平均分配,也不是论德行赏。
但要论长久广泛而重要的后天培养,你也没得选。
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在生命最初的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几年里,神经通路经历了深远而持久的成型过程。可以持续一生的基本性格形成了。无论你是被抱着,被人对你说话,被喂食,还是被置于能让你觉得安全的环境中、被悉心照料,你都没有任何选择,但这些都或多或少构成了你的情感骨架。它决定了你对威胁的敏感程度,你对新体验的开放程度,你的移情能力。
孩子们不需要对他们如何度过性格形成期以及这一时期给他们留下的永久印记负责。但他们无法摆脱它。

图源 MIMS Malaysia
从法律上讲,在美国,直到人们18岁为止,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自主的道德主体。显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成年年龄和成年标志(成年意味着成为道德主体),但所有的文化都标明了某种转变。
在某个时间点,一个孩子,一个本能的、不能完全对他们的决定负责的生物,变成了一个成年人,能够运用更高级的认知功能,按照公认的标准来塑造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并且,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要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观点而言,你把孩童和成人之间的界限划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出现在个体的气质、性格和社会经济环境确立之后。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节点。你满18岁了。你不再是一个孩子;你是一个成年人,一个道德主体,对你的身份和你的行为负责。
在这时候,你已经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你不仅仅通过先天和血缘的偶然结果被赋予了基因组成、种族和外貌。你的潜在基因特征也通过一种特定的养育方式,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借助一系列特定的经验,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激活”了。
你的基本精神和情感线路已经就位;你有特定的本能、偏好、恐惧和渴望。你有一定数量的金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机遇,一定的血脉家族。你接受了特定年限和质量的教育。你是特定的一种人。
你不需要对这些事情负任何责任,你还没有能力负起责任。你只是一个孩子(或者青少年,这更糟)。你的基因和你的经历不是你自己选的。先天因素和大量的后天因素都影响着你。
然而,当你满18岁的时候,这一切都归你了——全部的遗产,不论好坏。当你成为一个自主的、对自己负责的道德主体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像早已被一门大炮射出,沿着一道特定的轨迹移动。从道义上讲,你就像在飞行的半途中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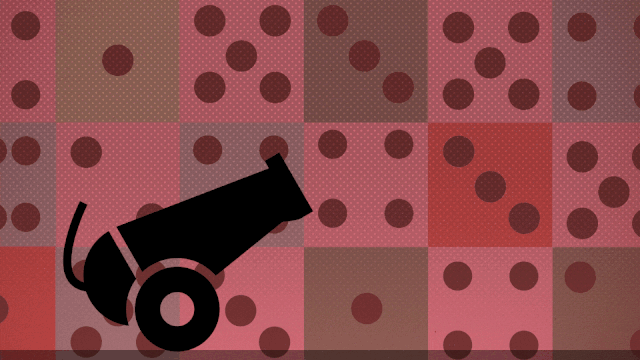
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如此。图源 Javier Zarracina/Vox
改善自我通常意味着克服我们自己的遗传特质
我们有多大能力改变我们的飞行轨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
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曾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提出一种著名的区分方式,能在这里派上用场。卡尼曼认为人类有两种思维模式:“一号系统”是快速、本能、自动的,而且通常是无意识的;“二号系统”则较慢、更为慎重,感情上更为“冷静”(它通常溯源到前额叶皮质)。
当我们成年的时候,我们的一号系统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已经固定了。那么二号系统呢?
我们似乎能够部分地控制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用它来塑造、引导,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我们的一号系统——改变我们自己。
每个人都熟悉这种自我挣扎;诚然,一号系统和二号系统之间的斗争往往是大多数人生活最戏剧化的部分。当我们后退一步反思时,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多锻炼、少吃饭,要更慷慨、少暴躁,要更好地管理时间,提高效率。二号系统认为这些是正确的决定;它们是有意义的;逻辑满分,合情合理。
但是当锻炼的时机来临,我们坐在沙发上,一号系统觉得它十分不想穿上跑鞋。它想吃油腻的外卖食品。它想对迟到的外卖小哥大发脾气。当需要二号系统的时候,它跑哪儿去啦?它姗姗来迟,满是悔恨和自责。我可谢谢你了,二号系统。
要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决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并通过日常的小决定来执行这个元决定。他们说,你是由你反复做的那些行为所定义的;我们的选择变成了习惯,习惯变成了性格。因此,形成良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反复选择做正确的事情,直到它变成习惯。
为了说得更具体些,我举个例子:出于某种原因,我讨厌等在别人身后。走在人行道上时,我几乎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走。开车跟在别人后面让我处于持续的、小火炙烤般的怒气之中。在商店里,看着排在我前面的人慢吞吞地付款,我真想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
当我使用二号系统进行思考时,我明白这种本能反应既不理性又不仁慈——不理性,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时刻等在他人身后,这没有办法避免;不仁慈,因为我指望别人高高兴兴地等我,但我自己却不能这样对别人。我让别人等我的时间和我等其他人的时间一样久,甚至更久,但是我死活等不了别人。
说得更直白一点,我在这方面有点儿混蛋。我也不想这样!这让其他人感到紧张。这让我很痛苦。它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一号系统和二号系统的博弈就如同《奇爱博士》里勃起的右臂与抑制其抬起的左手。图源 Giphy
改变这点的唯一方法是让二号系统思维凌驾于一号系统之上,一次又一次地干预我自己的愤怒,直到一种不同的、更好的反应变成习惯,而我则在字面意义上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更好的人。(呃,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
做一个好家长、存钱、交更多朋友,或是试图完成任何其他长期的生活目标也是如此;这通常包括克制我们自己的本能——其中许多本能对社会环境非常不适应。
人们用二号系统思维所做的事情值得道德上的赞扬吗?也许这就是精英体制的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真正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你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那么你很幸运!说真的——那也是运气
二号系统思维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运气的陷阱,原因有二:进行二号系统思维的能力和需求不是均匀分布的。
首先是能力。
用二号系统来规范一号系统是有难度的。通过用二号系统思维做出的慎重选择,发挥必要的自律来克服一号系统的反应是需要努力的。它很消耗能量。【要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参见布莱恩·雷斯尼克(Brian Resnick)对著名的“棉花糖实验”(marshmallow test)的有趣讨论。】
做到这一点需要一定的条件:一定程度的沉着冷静,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制于食物和住所等基本的物质需求,一定的训练和习惯。即使有这些优势,要做到也是很困难的。有一整个“生活秘诀”(life hacking)流派,致力于发明各类技巧和技术,可供二号系统思维用来抵消一号系统对咸点心和拖延症的偏好。
问题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拥有这些条件。你是否有能力、有多少能力用这种方式锻炼二号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猜的没错——你的遗传。它也取决于你出生在哪里,你是如何被抚养长大的,以及你能够获得的资源。
甚至,我们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愿望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的人生轨迹。
其次是需求。
有些人不太需要自律的能力,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失败都被原谅和遗忘了。比如说,假如你是一位像特朗普那样出身富裕的白人男性,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犯错、把事情搞砸。你总能拥有比别人更多的金钱和社会关系;司法系统总是会对你宽容以待;你总是会得到更多的第二次机会。你甚至可能有一天成为总统,而不需要学习与这一职业相关的任何知识或开发任何技能。
但是,如果你是一位黑人男性(举个例子),你就会被迫高度自律。你周围的人经常绷紧了神经,容易怀疑或害怕你,拒绝你的租赁申请,拒绝你的贷款,或是把你刷下去,转而招聘“更安全”的求职者,他们很有可能向警察告发你,而如果他们是警察,则更容易把你视为目标、对你滥用职权。

图源 Forbes
尤其是,如果你是个穷人,只要稍微越界一点点——学校里的一次事故、与司法系统的小冲突、愚蠢的青少年恶作剧——就可能招致数年甚至一辈子的恶果。底层群体必须付出两倍的自律,才能获得一半的机遇。
无论是自律的能力还是需求,都不是平均或平等分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穷人、饥饿者、无家可归或随时可能无家可归的人的要求要高得多,而这些人大概率是最难拥有培养自律能力的条件的。(这就是贫穷之所以代价高昂的另一个理由。)
你自律和自我改善的能力,以及你对它们的需求,都是你遗传的一部分。他们藉由人生的彩票落到你手中——靠运气。
承认运气的存在对幸运儿来说是极大的威胁
我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因为这事心生不快。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成就和优秀品质归功于自身。正如瓦尼所说,被告知自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掷骰子掷得好,这是一种侮辱。
当然,人们并不急于把自己的失败和缺陷归咎于自身。心理学家已经证实,所有人都受制于“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当我们评价他人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环境,而把失败归因于性格——然而当我们评价自己的人生时则恰恰相反。可以说,每个人与运气的关系都有点自私和机会主义。
一个人从人生这张彩票中得到的好处越多,否认这是张彩票的动机就越强烈。作为一个阶级,幸运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动机,将社会和经济结果塑造成一种天然的秩序的反映。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生的赢家们一直在讲述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他们才是那个特别的人。
但我对于运气之道德意蕴的观点正是如此:它们是根本性的,不可避免地腐蚀着既有的秩序。它们对每一种形式的特权提出质疑,对每一种使特权永存的机制做出阐明。
承认运气——或者更宽泛地说,对于那些并非我们所选、既不归功于我们也不归咎于我们的因素,承认它们对我们生活的普遍影响——并不意味着否认一切能动性。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一生全然是遗传所造,也不是说他们自身的品德不曾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起到任何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该为他们做的坏事负责或者因好事获得奖励。这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需要转化结构。在这场辩论中,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稻草人”。

图源 Christina Animashaun
不,这仅仅意味着没有人“活该”挨饿、无家可归、得病或是被奴役——说到底,也没有人“理应”获得巨额财富。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很大一部分源于运气。
巨额经济回报的承诺刺激了冒险、市场竞争和创新。如果监管得当,市场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赌博形式。试图将市场结果完全平均是毫无理由的。但是也没有理由允许饥饿、无家可归、得病或者被奴役存在于世。
我们没有理由不向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因好运获益最多的人——生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拥有某种特定的肤色,居于某个特定的经济阶层,被送到特定的学校,介绍给特定的人——要求他们付出些许,帮助那些没从人生彩票那里收到多少礼物的人。
而且,这两点是完全有可能同时做到的:一方面利用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利用市场创造的财富来鼓励不幸的人,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去。
“如果你想要任人唯贤的制度,”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在他开创性的著作《精英的曙光》(Twilight of the Elites)中提出,“那就去为平等而努力。因为只有在一个重视实际结果平等、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团结的社会中,机会平等和阶级流动才能盛行。”
正如在纽约州第14选区赢得众议院民主党初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喜欢说的那样:“在一个现代、道德和富裕的社会里,不该有任何人因为太穷而活不下去。”
无论是人类基因还是人类社会,都并不根据我们认为公平或人道的原则来分配人生的赠礼,因为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我们都会成长为成年人,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遗传,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开始我们的人生,被推向截然不同的人生目标。
我们不可能消除运气,也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减轻运气的严酷影响,确保没有人落后太多,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在实现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正视运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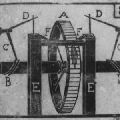 利维坦
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