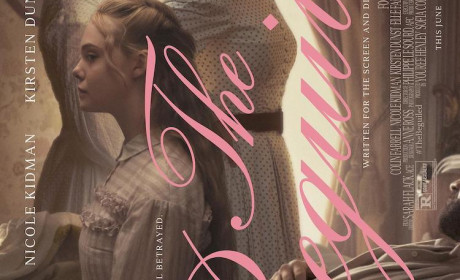《不可饶恕》:末路悲歌,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
出于某种不可控因素,我在大学时代几乎没有与朋友、老师谈论过西部片。作为一个在房间贴满约翰·福特、巴德·伯蒂彻、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海报,把萨姆·佩金帕的《The Wild Bunch》里四人持枪的场景裱进相框放在书桌前的西部迷,我着了魔似的十分害怕与我的社会学老师在吃饭时聊西部片的话题。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如此地讨厌凯文·科斯特纳和他的《与狼共舞》。

西部片的没落或许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谈资,因为在世俗文明的浪涛一泻万里的今日,溃退的远远不止是西部。古典主义小说、线下书店、切利比达克的布鲁克纳第八交,甚至是足球场上的古典前腰,这些曾经金光闪闪如同京都寺庙般的事物都已如人所见被时代齐腰淹没,而在历史巨人前进留下的众多脚印里,西部片的衰落或许是最自然也最无可避免的。
也许这么说有些过分伤感:每每当我慨叹西部的消亡时,我总是无可避免地想起伊斯特伍德的《不可饶恕》。这个饱含缅怀色彩的名词是夜幕来临前海潮褪去后左轮里的最后一颗子弹,自此以后,任何好莱坞产出的一部西部片,都是已死掉的灵魂,伊斯特伍德本人的作品亦如是。

《不可饶恕》上映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的1993年。在它问世的三年前,凯文·科斯特纳用他那部饱含民族主义质问的《与狼共舞》彻底将老派西部片的荣光击碎。属于萨姆·佩金帕和乔治·罗伊·希尔的辉煌的1969年之后,时隔二十年,西部片最后回光返照的时刻才终于来临。《与狼共舞》上映后三年,属于老牛仔真正的告别时刻便遽然降临了。从那以后,西部片里的个人英雄主义彻底死去,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加里·库珀、艾伦·拉德和约翰·韦恩了。
影片里伊斯特伍德的第一次出场就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凉意味。当斯科菲尔德小子找到隐居的杀手威廉·莫尼时,老牛仔的身躯被堪萨斯的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恍若漆黑海边的微弱篝火,泥泞的西部农场让老朽的伊斯特伍德狼狈不堪,让人几乎忍不住发笑。然而从这时起,我也已然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凡者的故事。

与所有反英雄的元素不谋而和,老牛仔接下悬赏的原因是养活两个孩子和农场,这种与所有正义、传奇背道而驰的谋划,让老牛仔在观看者心中地位一降再降,老派西部片里炎炎烈日下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美国中西部昏暗的天空和湿冷的雨水。
征途中,奈德因为觉得不对劲而询问斯科菲尔德小子是否看到天空最后的老鹰。“我能一枪把它打下来。”小子笃定地回答。然而事实是天空中并无老鹰,小子也是个睁眼瞎。这样一种在西部片里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行动笨拙的老牛仔和视力极差的小子组成了一支荒诞的队伍。这是牛仔时代结束的隐喻,孱弱的队伍走向悲凉的结局,似乎一切行为都已经不再由英雄气概驱使,而是由无力本身。

不出所料,生病的伊斯特伍德在酒馆被警长“小比尔”痛打了一番。
当“小比尔”质问眼前的这个牛仔的名字时,曾经威震西部的杀手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在老牛仔持续默默忍受毒打的镜头中,怀抱着找寻老派西部片初衷的人们会渐渐地陷入无比的失望和愤懑:“这不英雄气概,这不西部、这甚至很窝囊”。但,这不是现实吗?那些慢慢消逝在时代浪涛里的伟大事物,在今日之所以会成为老古董、保守派的代名词,不是因为它们改变了、衰老了,而是因为它们永不可能是伟大的时代的敌手。

雨季来临的怀俄明州不论是白昼还是黑夜都一概昏暗不已,昏迷的老牛仔在半睡半醒中梦见长着蛇眼的死亡天使、幽冥河和亡妻克劳迪娅,死亡的氛围绝望地环绕在垂死的伊斯特伍德周身。一个身经百战的杀手开始畏惧死亡,导演有意让这样畏死的形象不停浮现:牛仔也只是挣扎的浮萍。在生死更迭、风雨如晦的时代,没有人不会为存在本身困惑、疑惧,那样去决定别人的生死和被别人决定生死,充满了宿命论的现代反抗。
所以,在面对可以决定别人生死的时刻,伊斯特伍德饰演的威廉·莫尼也好、老奈德也好还是小子也好,总是反常地沉默不已。老派西部片里快意恩仇的惩奸除恶早已消失,人们反复思考的不仅仅是自我的生死,还有他者的生死。那样和自己存在紧密联系的真实感,它们在被自己亲手杀掉的人身上残留,屠杀的痕迹会消弭掉一切杀人的快感和真实感,而只留下对生命消散的无尽敬畏。

“我宁愿目不识物,衣着褴褛,也不再要这笔钱。”小子永远地交出了他的斯科菲尔德左轮。
“我再也不会杀人了。”
拿到左轮的伊斯特伍德却要开始一场真正的屠杀。
当得知自己最好的朋友奈德被“小比尔”虐待致死时,威廉·莫尼为自己屠杀妇孺过往的无数次忏悔似乎与自己的仇恨化合了。他再也不是软弱的老牛仔,而是一个凡者。为了复仇而杀人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除生的痕迹,而是对生的另一种唤醒。当恶(杀人)在我们不可知的地方被赋予最重要的意义时,它反而比无作为的非恶要更恰当,更富含生的气息。

伊斯特伍德开出的最后一枪就成了最后一部西部片的最后一枪。这颗子弹将传统和没落的现实统统穿透,在触碰到普遍的生与特殊的死的时候,它善意地选择了屠杀,而不是一退到底,彻底将最后的恶吞咽进最后一个牛仔的喉咙。伊斯特伍德从这时起,完成了既非英雄也非反英雄的壮举,凡人的生命第一次如此接近神明,这在西部片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要妄言的是,伊斯特伍德恐怕并未想要证明这种复仇的壮举是在唤醒生的本质与恶的唯一性。但是他为了让一个牛仔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作的努力,成功让没落太久的西部片重新发出了它最后的尊严的光。这光芒在怀俄明的雨夜里熠熠生辉,恍若京都夜晚焚毁金阁的火。
也许在《不可饶恕》之后,西部片依旧摆脱不了英雄末路的悲情,但这样一个饱含诗性和不灭意味的收尾,又如何无法带给西部片真正的、永远的生呢?

 影形人
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