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托》男人打了他几下板子 手像被烫了一样往回缩
我愿意以纯真的平静来描画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Ricordi Racconti埃内斯托生谁的气都生不长。他总是很快就原谅别人,也希望很快就得到别人的谅解。经过一夜的担惊受怕和辗转反侧,到早上男人就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不仅为了安抚当下不安的心灵,也是想责备他昨天的莽撞和暴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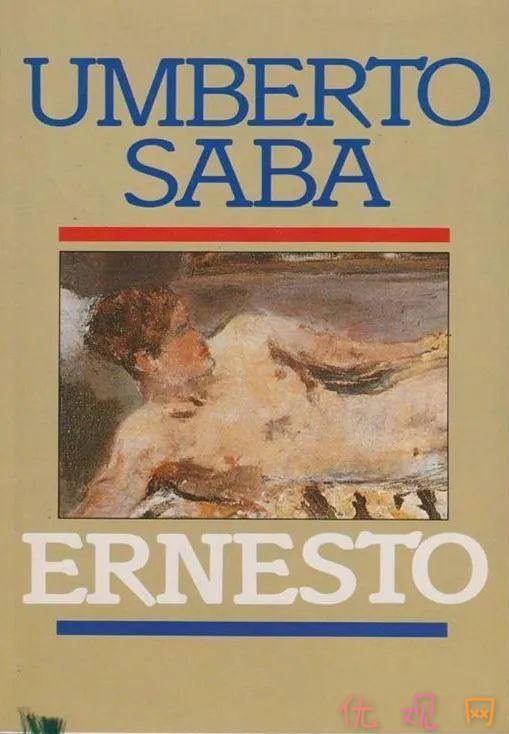
男孩像平常一样准时。他兴致勃勃地来了,手里提前准备好仓库大门的钥匙,好像很着急要开门。
生了几天的病让他看上去更茁壮了,一个热水澡让他看上去更柔嫩,他可着实好好泡了一会儿呢。经过了一夜的困扰和怨愤,男人明白他仍旧爱他——越发爱他了。只是在他的爱中存在那么点施虐,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或试图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尽管他用埃内斯托昨天的大喊当做他的托词。可是我们很快就知道,他的这种行为,开展得并不顺利。
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他问道,他一点都没有被保证母亲既没有听明白、也不会乱猜疑的话说服。
拿我怎么办?
该打多少板子?他解开埃内斯托的裤子,遵循他们往常的程序,男孩仍旧站着,双臂在两侧举起。
我还以为你要给我蛋糕吃呢,他说。(男人有时候给他买蛋糕,这是他唯一买得起的礼物,也是唯一…不会留下痕迹的礼物。埃内斯托从来不讲虚假客套,当场就吃光。)我只想让你开心,你为什么还要打我?
当做小小的惩罚。
小小的惩罚?如果我做的哪里不对,也不该你来惩罚我。
我告诉过你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大喊锥形物的事?
是这个,也不全是。你太好看了——还总是戏弄我——开个玩笑,就让我犯傻了。
埃内斯托很委屈自己被当成了戏弄者。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英俊;他从不在镜子中观察自己。他果真戏弄他的话,也是出于无心。
男人情不自禁:他在埃内斯托光着身子的那一部分打了一巴掌。没有太用力,但还是在埃内斯托的肉体上留下一个鲜红的手掌印。
别打了,他生气地说,用手捂住被打的地方。摸起来暖暖的。这时候他看到男人像往常那样开始不断抚摸他,像在忏悔,他说,赶紧的,开始吧。
那天男人的愉悦感比他有生以来所记得的都更强烈。但是埃内斯托感到了厌倦,并决定这是最后一次。他们穿好衣服后,男人出去了几分钟,买回来一包价格不便宜的蛋挞:酥皮牛角里有黄色的奶酪冻,一个要花四个铜币。这是埃内斯托最喜欢的糕点,看到蛋挞,他现在可不懂得拒绝。出于礼貌,他让给男人一个,男人照例拒绝了,埃内斯托吃了三个。然后他坐在男人身边,那个往常就放在那里的面粉袋上。两个人都不想着手开始工作;男人不想缝补破口袋,埃内斯托也不想回他那个挨着老板书房的、当做办公室的小屋,几乎有一周的工作等他处理。
你在想什么,男人问道。
埃内斯托大笑,我在想那老家伙,他说。
别管他。
我不明白,埃内斯托开口道,尽管他下定决心以后不再满足这个男人的欲望,但是他对他毫无恶意,喜欢和他说话。当他以后第一次读到蒙迪翻译的《伊利亚特》,并沉浸其中,他把尤利西斯想象成这个男人的身体。就这件事而言,如果他和男孩处于同一阶层,——至少灵魂上平等——而不是一个贫穷的日间劳工;换句话说,如果他能对他有所指引,帮助他对自我进行认知,那么报偿就不仅仅只偏向一方,关系可能维持得会更长久。不过眼下……
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忍受我到现在,没有一脚把我踢出去(我正求之不得呢)。你都不知道我干了多少坏事……
你都干什么了?男人被他公开希望让怀尔德先生把他开除的声明所震动。他不知道男孩有什么新打算,他已经开始考虑一旦如此他们以后在哪见面。也许晚上在郊外?但是男孩不能、也不愿意下班后约会,并且,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的地方了。埃内斯托总是说得对,他想,是他首先建议的这个地方。他给怀尔德先生的货车装卸货物,几乎拿不到足够的工钱,就是为了接近男孩。
老板受不了卫生球的气味,他说那种气味让他头疼。我就在每个角落都放了卫生球,还有家具下面。他大发脾气,要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气,他这么说。他以为是清洁女工干的,第二天他冲她大喊大叫:说她用了过多的那东西,也不事先开窗。可我干的可远不止这些呢。
还有什么事?男人照例被男孩的话引发了巨大兴趣,尽管他怀疑他讲的一些故事都是编的,至少是夸大了的。
很多事呢,埃内斯托说道。首先,你并不知道他经常用德语写上四、五页纸的信吧,因为我只用意大利语写信。商务信函写这么长没有用处,但是他……他就是很狂热,尤其是给Louisen Muhle(路易嘉·米尔斯)写信的时候,那是他的主要供货商;他花上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给她写信。大概到五点钟信写得差不多了,他就出去喝咖啡。我就舔舔手指,在他信纸的第一页或第二页上抹一下子,看上去像墨水的污痕。他回来看了,像个土耳其人那样咒天咒地,还要再重新抄写一遍。我在隔壁房间笑得肚子疼!
他就没发现过吗?男人半信半疑地问道。
从来没有。反正他从来没提过。他还特别受不了街上的孩子(就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群孩子):他们和卫生球一样坏。所以我雇他们(他的确雇了他们,但不是用钱:用信封上截下来的邮票,穷人的孩子把它们当货币),叫他们互相追逐,从一边门进,另一边门出。从一开始老家伙就不知道是我背后指使的。他威胁叫警察,但他需要的并不是警察!还有,有一天我自己想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花招。
男人听得津津有味,却仍有疑虑。他不知道——也不肯叫自己相信——埃内斯托从来都很诚实;因为埃内斯托是个正直的男孩……然后他想起他大喊锥形物的事,这才倾向于相信他的话了。
你想到什么花招?
不仅想了,而且还做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经常戴的那双金丝雀黄的那副手套,最近不戴了吗?一直到我们最近……我特别看不惯。那副手套的颜色,还有他总是戴着的那个德行样……真恶心。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住在附近的另一个男孩(同一个学校的)拟定了计划,买了一些酸豆粉。你知道酸豆粉的颜色和……那个东西的颜色一样,在办公室开门之前,我把酸豆粉抹在两个门把手上。我一看到老板来开门,我就去开另一个门进来。我吸了一下鼻子,闻了一下我的手,确保他看到我了,然后就大喊屎!有屎!那个小混蛋在我的门把手上抹了屎!老家伙的眼睛投向手套——弄了一手套。他怎么会知道那仅仅是酸豆粉?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了,他真的是差那么一点就识破我了。他摘下手套,扔进了垃圾桶。他那么小气的人,肯定随后又捡回来,洗干净了。他之后就没戴过,或者说,我没再见到他戴过。
男人大笑,他听得越发津津有味了。
但是灯的故事才是最有趣的。一个晴朗的冬日午后,我买了一小盒的帽盖儿(这里的人们都把它叫做amorfi),孩子们用玩具枪当子弹用的,他们就听一声响,无伤大雅,也不值什么。我把它放到煤气灯罩下,点燃燃气灯,盖上盖儿,看看会怎么样。砰得一声响,灯罩就碎了,这可想而知。他开始咒骂,就派人去买新的。他从来都不一次多买几个。这时候我也放了一个帽盖儿到我的灯盖底下,灯罩也坏了。于是他就对灯罩销售商勃然大怒。他说他们为了多销售就故意捣鬼,当然我尽可能站在老板这边,跟着义愤填膺;我附和说,这些灯罩销售商都是些贼,简直不是人。我一直都很走运,因为那个人去买新的灯罩(你还没见过他),却空手而归:商店断货了。我们只能到更远的商店去买,天知道要等多长时间,但是老板想写完他给Louisen Mahle的信函,而且他已经受够了。他派那个人回家,从他老婆那里去借汽油灯,然后他照常出去喝咖啡,看他的民族性报纸,因为他从不看Piccolo这种意大利报纸,永远都在看Frankfurter Zeitung这种诸如此类的德国报纸。——有次我去咖啡馆去接他,他就在读这个报纸,那时候一个工厂主突然来了,着急想和他说话呢。再回到那个美好的下午,就在他回来之前(我在门后哨探),我把借来的汽油灯放到一桶水中泡了一下,玻璃又碎了。他甚至都没生气——他都没有力气生气了;他向命运低头了。可那傻瓜还不知道我就是他的克星。
看看你有多么该打屁股,男人温柔地说。
别提打屁股,那时教训小孩子的。我还搞不懂他为什么还不明白是谁在捣鬼。
他爱上你了,男人说,他很快就发现在别人身上也有自己的那种癖好,假装不知道,也就没有开除你。
埃内斯托做了一个恶心的表情。
你不要以为我和你做这种事情,就和别人也做。况且,他那么老了(实际上老板并不老,但是在埃内斯托眼中,所有三十五岁以上的男女都是老人,几乎是半截入土的人了),而且也结婚了。你没看到他的老婆有多漂亮吗?她也有胡子——跟你的似的。
我只是不相信他猜不出来是谁在和他玩恶作剧。
没准他从来都没猜过:有一天我们在街上遇见,他甚至还送我一柄有银把手的手杖。——实际上他一直都带着。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当然我谢了他——我还能做什么呢?——就好像我特别喜欢他的礼物似的。
男人非常吃惊。
你难道不喜欢礼物?
喜欢,但你指望我拿一柄手杖做什么呢?我既不是老人,也不是那种油头粉面的家伙,我从来都不带手杖。我只好放在家中,交给母亲当做奖品保管——她儿子赢得荣誉的象征……她要是知道实情的话!
知道什么实情?
我对老板做的那些可怕的事!现在我不再这么做了,好久没有那个冲动了。他太蠢了,甚至故意惹他发火,都不那么好玩了。
埃内斯托开怀大笑良久之后,充满稚气的脸上笼罩了一层忧伤。过几天我就十七了。我得继续工作,很快就要考虑如何养活我和我的母亲。后天是我外婆的生日,我需要考虑一下送她什么。
你原来还有外婆?
我当然有外婆,我很爱她。我可不是唯一一个爱自己的外婆的人,有一位仍然健在的伟大诗人,他也爱自己的外婆。他就是邓南遮(d'Annunzio)。他现在肯定老了,但还是为她写了一首长诗。长诗叫做Alla Mia metrice(献给我的保姆)。我的一个表兄从他们印刷这本书的地方,给我寄了一本。写得美极了,——总之我非常喜欢,几乎记在了心里。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男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看上去很恐慌——他的确也很恐慌。
我忘了是不是跟你说过,埃内斯托继续说,我跟我外婆在她的乡下房子里长到四五岁大。起先是母亲因为悲痛不已,没有了奶水。然后她做起了家具生意,就没时间照顾我了。她说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就没有过片刻的幸福。她经常生病,所以她特别开心能把我给我外婆照管。
你想送她什么礼物呢?
送她一斤咖啡,一斤糖,埃内斯托回答。因为他是一个既严肃又实用的孩子。她很穷,我想这些东西对她有用。但我不知道我的钱够不够。
(男人多希望自己能给他一些钱啊!但即使他手头充裕,也不敢开口,因为男孩可能会感到是冒犯他——他可能会以为给他钱,是用来换取他的满足感的。)
你就让我想到了我的外婆,埃内斯托继续说,当你你跟我说,因为我的那声大喊和那些恶作剧,就该打我屁股,我说那些都是教训小孩子的时候。
你外婆打你吗?
我记不太真了。但是她说她偶尔打我,而且下手很重。她说我一哭她就心软了。也许对于我外婆来说,我的确该打,但是你没理由打我。说着他严肃地看着男人。
说话间,男人起身,赶紧取下仓库大门的门闩。开门的时间到了,他不想让老板或者别人发现门反锁着,他们单独在一起。几乎没人会多想,但是男人的良心并不清白,他始终都或多或少的,感到紧张。
我把它带过来了,男人次日说道。
带什么了?埃内斯托兴趣不是很大。
板子。
做什么?
送给你,男人顽皮又大胆地说。
埃内斯托眼睛瞪大了。
给我看看,他说。
男人从麻袋后面取出一个白桦木魔杖给男孩看。他正好途径博斯凯托,在那里他悉心挑选了这个特别的魔杖,新制作的,又很有弹性,能够猛烈地刺痛肉身。
跟我看看。
你答应还回来的话,就给你看。
那可不好说。我说了,快给我。
他被男孩专横的口吻打败,把魔杖给了他。
现在把你的手伸出来,埃内斯托说,像这样——他抓住男人的左手,摊开,像小学班主任逮住不注意听讲的学生,想要惩罚他们那样。
男人又一次遵从了。埃内斯托抓着男人的手指尖,摊平,稳住。他晃了晃魔杖(好像要试验一下韧性),并狠狠抽打下去。男人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了,他的手像被烫了一样往回缩。他上下煽动手掌,用空气给手降温。
埃内斯托大笑。
你要打我多少下?他问。
五下,他天真的回答。
埃内斯托把手伸到后面,摸摸自己的屁股,好像他的屁股已经被打了一样。
你不经主人允许就擅自做主,他说,记起他常听他舅舅使用的一句不那么适用的表达方式。他大笑着把白桦木魔杖折成几段,扔掉了,就像他们曾经第一次做的那个下午,他扔掉高级面粉袋上撕碎的标签那样。
现在开始干活吧,他简短地说,就像领导在命令下属一样。但是当他意识到男人是那么沮丧,他和蔼地找补了一句:
抱歉我弄疼你了。我只是想玩玩,就像你想玩玩一样,我知道(他并不知道——可以肯定真实的意思是在他话的反面)。如果你感到有一点点疼的话,请记住,是我带给你的疼痛,埃内斯托。然后,你就不会感到那么疼了。

 影形人
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