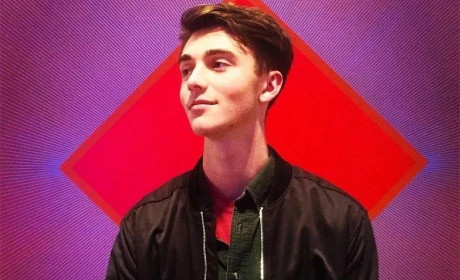King Krule:害怕伦敦,恐惧飞行,讨厌采访,想来点锯齿感粗糙的朋克

身为King Krule,Archy Marshall是个才华横溢的城市顽童,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奏出了集dubby、爵士曲风和锯齿般听感于一体的独特音符。现在的Archy Marshall当上了爸爸,并从南伦敦迁居至维甘,最终看到地平线上的曙光。当他重返伦敦时,Tom Doyle在他的家乡主场见到了他。
英格兰默西赛德郡克罗斯比海滩,日落时分。地平线虹光散射,天上乌云散布,本名Archy Marshall的King Krule站在天地之间,抱着电吉他弹奏起新作《Energy Fleets》的乐曲框架。他柔软的人声没有被扩音放大。而他的搭档、摄影师Charlotte Patmore刻意为他拍下了一卷镜头晃动的录影带。
在Archy Marshall以“King Krule”的名义发布的第三张专辑《Man A live!》中,这首歌是跟随16分钟微电影《Hey World!》同步首发的四首新歌之一。这段低调又充满艺术颗粒感的音乐短片,摄于英格兰西北部的一片雪原上,背景中有几座冷却塔在吞云吐雾。2019年,女儿Marina出生后,这个南伦敦人就搬到了此处。

△Archy Marshall:“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喜悦,其实就是所谓的‘视力距离’。”
25岁的Archy Marshall从小在南伦敦的Peckham和East Dulwich长大。当生活从大都市切换到别的省份,他感觉到一种释放,摆脱了自青春期就患有的城市生活幽闭恐惧症。
“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喜悦,”他说,“其实就是所谓的‘视力距离’。我记得自己曾读过一篇研究报告,对比的是纽约孩子与其他地方孩子的不同。纽约小孩的面前总有形形色色的砖墙,所以他们的视力与其他地方孩子的视力完全不一样。”
“我的身体更健康了,精神上也感觉到更强大。我花了很多时间保持静默。”
在短片《Hey World!》中,你能看到Archy Marshall举目望向广阔天地,如地平线般开阔的视野刺激着他的神经。对此,他已渴望了许多年。早在2017年,他就说过想要离开伦敦,或许前往英国南海岸荒凉凋零但美丽的海岬Dungeness去居住。后来,妻子Patmore怀孕了,这个决定对他而言就变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考虑搬到距离她住在维甘(Wigan)的父母更近的地方。新鲜的北方环境再加上自己晋升为人父,这两件事共同把这位歌手从不安抑郁的情绪阶段中拯救了出来。
“伦敦的生活很难,这是一座无序蔓生的巨大城市,到处都熙熙攘攘的。我觉得,就这里实际存在着的东西而言,南伦敦显然是个奇葩。”
“这(指搬家)帮了我很多,”他说,“我的身体更健康了,精神上也感觉到更强大。我花了很多时间保持静默。”
但这并不是说Archy Marshall就此遗失了对家乡的爱,他的音乐依然是浓郁、晦暗的,深受南伦敦氛围的熏陶。“从某种意义上说,伦敦的生活很难,这是一座无序蔓生的巨大城市,到处都熙熙攘攘的,”他说,“我觉得,就这里实际存在着的东西而言,南伦敦显然是个奇葩。”

“但现在,再到伦敦来我就很兴奋,”他精神奕奕地补充道,“像个孩子似的觉得,‘哇,我可以出门,看看各种东西、各种人。’走出自己家门口,就有很多能做的事。人们总是倾向于欣赏事物的本来面目,但如果能从其中抽离出来,感觉就会很好,浅尝辄止就够了。”
然而,为了再尝尝伦敦的味道,Archy Marshall不可避免地要重蹈过去那些不健康的覆辙。采访当天,他和朋友前一晚一起宿醉的难受劲儿还没过,就坐在Battersea的一间酒吧里,发出轻轻的呻吟。他点了一个汉堡,上菜后,却又拧着鼻子把食物推到边上。
也许一想到要面对本刊的采访,他就有点反胃。十几岁时,Archy Marshall第一次在家里录制自己的歌,那时候他会坐在马桶上,幻想自己被采访的场景。后来一切成真,他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被迫应付那些关于个人生活和音乐创作的问题。早在2017年,他就有计划要和本刊聊一聊,结果却在最后时刻放了鸽子。

△2013年,Archy Marshall在德国的Melt!Festival上演出。
“我特讨厌读那些写我的文字。”他解释道,咧开嘴笑的时候露出了一颗金色门牙,这让他有了一股坏男孩的气质。“是的,我讨厌采访,因为我就是我,我不想读那些写我的文章。我对自己了如指掌。你知道我说的啥意思吗?”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采访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不愿面对的事情?
“是啊,当然了。采访时我会忍不住自言自语‘:哦,拜托了,闭嘴吧伙计。’”
问题的一部分还在于,Archy Marshall经常在歌词中残忍地忏悔自己内心世界的慌乱,于是如果要他在采访中进一步解释自己,他就会觉得很局促。《Man A live!》这张专辑,是在伦敦和Stockport两个城市、两种思维之下创作的,其中一首名为《Stoned Again》的歌简直是一个妄想症患者的尖叫,它如实反映了伦敦生活的样貌,唤起他十几岁时如涅槃乐队般嚣张膨胀的自我记忆。“这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歌,只是有些戏剧化夸张了。”他如此解释。
当时,Archy Marshall已经在伦敦南部的Maudsley精神病院接受了各项心理健康问题的测试,不过还没有得到定论,但失眠和抑郁仍然是他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作为“King Krule”发行的第二张专辑《The Ooz》[译注:Archy Marshall和他的哥哥曾组过一支叫作“Dik Ooz”的乐队,玩了个将“Zoo Kid”倒过来拼写的文字游戏,而专辑《The Ooz》是他对这种文字游戏和“The Ooz”概念的延续],其中的单曲《Biscuit Town》就有一句歌词赤裸裸地写着:“我猜她认为我有躁郁症。”
他是幸运的。父母虽然已经分居,但都各自鼓励儿子接受更多治疗,鼓励他的艺术追求。从小到大,他都被他妈妈挂在家中墙上的巨幅画作所围绕,那里面有费拉·库蒂[译注:Fela Kuti,尼日利亚爵士音乐人、afrobeat音乐创始人、多乐器演奏者、民权运动人士]和史努比·狗狗(译注:Snoop Dogg,美国说唱歌手)等人的肖像画,这鼓舞起他对视觉艺术的热爱。而他爸爸曾经送给他一台八轨录音机,让他更直接地走上了音乐人之路。
在成为King Krule的过程中,Archy Marshall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声音世界,这促使他创作出一种真正的原创混合风格:低音强拍的bassline、1990年代的神游舞曲、类似Chet Baker的爵士低吟和Eddie Cochran式的rock’ n’ roll slapback echo vocals。“是的,这就是我想要的风格。”他点头说,“但我也想玩点儿快速的、锯齿般粗糙的朋克。”
他曾经就读的Brit School,是一所位于Croydon的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的学校。就跟校友Amy Winehouse一样,他也觉得自己与那些技艺熟稔的高级乐师和牙齿锃亮的音乐剧学生们格格不入。“很多学生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他笑道。他逃课去酒吧演出,试图发展出一种叛逆、吓人的舞台风格。他那样做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吗?还是仅仅源自青春期的叛逆愤怒?
“不,那只是我个人的舞台处理方式而已,”他解释道,“盯着人们看要比目光低垂、看上去弱不禁风容易多了。你知道,人在年轻时经常听到一些‘道理’。人们会告诉你:‘噢,你弹吉他时不能看着吉他,你演出时不能突破你扮演的角色。’你当然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啊!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Archy Marshall上传到Myspace的歌曲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对他是个关键性的认可。Mike Skinner和美国独立乐队Girls也对他的歌曲做出回应,后者还将他推荐给美国厂牌“True Panther”,此后的Archy Marshall才得以与英国厂牌XL签约。其他艺人的认可也接踵而至:Beyoncé说自己是他在2013年发行的首张专辑《6 Feet Beneath The Moon)》的粉丝;Will Smith的女儿Willow Smith则翻唱了这张专辑的开场曲《Easy Easy》,这首歌里引用了许多非常英国的文化元素,比如“鲍比”(译注:bobby,一种热情、护短的英国男人的形象)和某家英国连锁超市的名字。
“当然啦,知道这些人和我的音乐沾上边的时候,我心里一阵激动。”他说,“Willow Smith,我从小在电视上看着他爸长大,天天看。每天放学回家,我屁股一坐,就开始看《茶煲表哥》(译注:Willow Smith主演的美剧)。我也会去电影院看Willow Smith的电影。所以说,当我确信他的孩子非常喜欢我的音乐,喜欢到想去聊聊关于乐购(译注:Tesco,英国连锁超市)的话题时,这事是多美妙啊。”

△轰炸机指挥部:King Krule的尘土之国,2019年12月16日,伦敦克拉珀姆。
哗众取宠的言论和大胆告解的歌词,使得Archy Marshall像他的许多前辈那样,被誉为“发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而这样的名头堪称“金杯毒酒”。当本刊记者提起这个说法时,他耸了耸肩。
“我本人不是很在意这些说法,”他说,“我写《Easy Easy》时大概十四五岁,很多人说这是一首很有社会观察力的歌。但对我来说,它只是我对自己当时生活的地方的瞎扯淡而已。而专辑《The Ooz》只是我想变得特别怪异的一个习作。”
《The Ooz》是Archy Marshall在“King Krule”名下创作的第二张专辑,这是一张肆意奔放的杰作,但在此番创作之前,他经历了一段严重的创作障碍时期。因为他想试着直接在笔记本电脑上做歌,而不是先用人声和吉他把歌曲简单地写出来。“搞不懂,”他叹气道,“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我的灵感还不够,有特别多的想法,但就是没有一首歌能完全成型。”
当阿根廷萨克斯乐手Ignacio “Galgo” Salvadores给Archy Marshall发了一段他在东伦敦一座桥下表演的视频,灵感终于降临。“见到他真是天意,”Archy Marshall激动万分地说,“我给了他麦克风,还有延迟效果器之类的东西,就让他开始走起来了。然后他那部分就成了我那张专辑中重要的组成。是啊,这其实是一个由意外和信任共同打造的成果。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拉别人入伙是件很难的事。”
专辑《The Ooz》将King Krule的古怪发扬光大。其中两首单曲的MV体现得尤为明显:一首是《Dum Surfer》,Archy Marshall在里面扮成了一个平躺在医院手推车上并现身于演出现场的人;另一首是《Czech One》,这回他坐在飞机上,左眼蒙着绷带。很明显,他并不想让自己去展现那种光辉四射的流行明星形象。但为啥非让自己看起来病恹恹的呢?




King Krule的专辑大碟:2013年的《6 Feet Beneath The Moon》2015年的《溺水的新地方》(以Archy Marshall的本名发行)2017年的《The Ooz》2020年的《Man A live!》
“因为有很多歌都和‘内伤’有关,”他说,“所以MV就间接地把‘受伤并疼痛’展示给观众。你懂的,这样你就可以亲眼看到伤痛了。而我不必逐字逐句地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
King Krule在听感和视觉上的刁钻角度不断地吸引着其他艺人的注意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艺人们。Kanye West来找他合作,但那时候的Archy Marshall表现得像个拽上天的小孩,简直令人错愕,他在一次采访中甚至说自己“不能被别人打扰”。Frank Ocean也想和他在录音室里碰出点火花,但他们的合作只不过进行了两次会面就没能继续下去。
“我认为我有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今天的Archy Marshall解释道,“而且,有时候你不知道人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有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我对别人的态度一直没把握。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有多少空壳合作是被批量制造出来的......就像是要搞一个全明星阵容一样,我对此一点欲望都没有。”
“但我喜欢那些人的音乐,”他接着说,“只不过有时候真的没必要扑上去和他们合作。”
一个事实就此凸显出来了:就创作而言,Archy Marshall有点儿独行侠的感觉。“一般情况下,真的很封闭,”他这么描述自己的音乐创作过程,“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做歌的。”
这种仿佛让灵魂在深夜时分得以净化的亲密感,在专辑《Man A live!》中非常明显。其中一首歌《Perfecto Miserable》的开头是一段电话转接到语音邮箱的录音提示——Archy Marshall试着打给一个明显不会接通的电话,紧接其后的绝望情歌,揭示了他对孤单寂寞和暗黑念头重返的恐惧。
“是啊,那真是一首很惨的歌。”他说道,突然变得讳莫如深起来,“我是在一个晚上写的这首歌,当时我不太开心。所以,嗯......”
在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中,Archy Marshall不再沉湎于自己的问题,而是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其他与自己有共情感受的人。在沉静、给人以慰藉的《Alone,Omen 3》中,有一句重要的歌词写道:“沉入低谷没什么不对/但别忘了你并不孤单”,这句歌词饱含着他的同理心......

 Qthemusic
Qthemusic